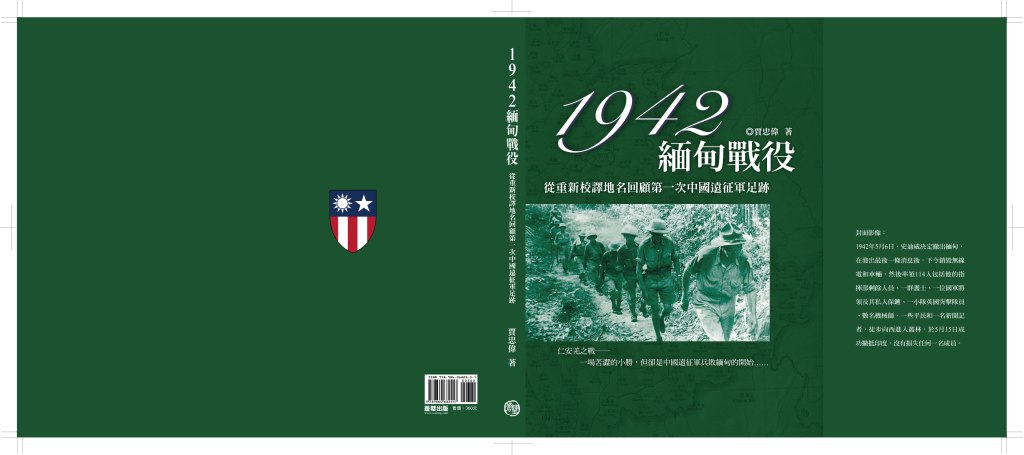在當前的大時局下,偶見新出現的這個視頻的平台「佐榮寫真館」,
其中稱「有照片,才有真相」。
然而,配合著那些圖片的口白內容,那真的是『真相』嗎?
其實不過是有心設計出來的『懶人包』吧!
個人看了本視頻之後,感覺很痛心,因而不能不寫出這一篇來──
『中華民國轟炸臺北?臺灣人的戰時生活』
其中提到兩個重點──
其一,關於當年我島上總督府招募志願兵,應徵者踴躍的問題──
在這個視頻中,他們找來種種相關的照片,然後,配上這樣的口白文字──
「1945年,開始實施對於台灣本島人的徵兵。在此之前的1937年開始,則是公開招募非戰鬥性任務的文職、翻譯、農業、運輸、工程、航運的軍屬人員。
1942年,總督府對外招募陸軍第一回特別志願兵,名額是1,020人,結果應徵報名的人數高達了425,921人,佔當時台灣青年人口數的14%;而錄取率就只有0.2%而已。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第二年再招募第二回志願兵的時候,名額是1,008人,結果應徵的人數達到空前的601,147人,志願上戰場,是要有為國家捐軀的覺悟,難道會有人把死亡當成是兒戲的嗎?從上面這些驚人的數字看來,如果還有人再繼續說,台灣人是被迫從軍的,被拉去當軍伕,那真是對我們先人的熱情最大的侮辱」。。。。〈6分28秒~7分35秒〉
看哪,引用出懸殊的數字與熱烈激憤地宣告,是多麼的動人。。。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在該影片中只提到了社會經濟上的統制與配給;卻沒有提到,至1942年之際,社會上普遍的生活如何,配給夠吃嗎?不夠吃,買得到嗎?請看以下是當年的史實──
「戰況一天比一天激烈,……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的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她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老百姓的生活如此」(《無情的山地》,林彥卿著,頁131。2007年二版一刷)
「體力測驗……母親為我準備的新內褲出了問題……當時已經沒有全棉的布料,都是使用人造絲,品質很不好。連內褲的小繩子也是人造絲造的,拉力不夠,所以開跑沒多久就拉斷了,內褲都快要掉下來了,……」(《台北三中末代學生記》,賴麟徵著,台灣風物五十七卷二期,頁38。)
「物資嚴重缺乏到連養豬人家的餿水桶裡,只要上頭飄著番薯的蹤跡,馬上就會有三、五個人靠過去搶著撈來吃,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女主人看到了就說:『阿品,番薯都給你們撈去吃了,那我的豬要吃什麼呢?』被人這樣說很難為情,但是肚子餓起來的時候,什麼尊嚴啦!面子啦!誰也管不了那麼多。」(《怒海孤舟‧一位體殘心不殘的素人作詞家的故事》,簡明雪著,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編印,頁38。)
這些應該就是大量志願兵應徵的最大理由,是否軍中要抗敵,應該一定能吃得飽?所以……?當然,另一理由,是可以不「志願」嗎?
至於是否「當兒戲」的問題,當年竟真不乏這樣「兒戲」的紀錄──
「對接受教育敕語長大,搆得上成為軍國少年的我們而言,最憧憬的是日本軍人和畢業的軍屬的英姿……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好像參加畢業旅行……」
據稱,這種「無知」,要到幾個月後──
「第一次親眼目睹戰爭的殘酷景象,我嚇得全身顫抖,在這之前,那種畢業旅行的氣氛一下子全部消失無蹤了。」(《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濱崎紘一著,邱振瑞譯,圓神出版,頁47~50。)
或者,所屬的單位中,有比賽「志願」的,或起帶頭作用的,能不為單位的榮譽而「志願」嗎?
據稱,還有在東京讀書的兒子,「竟然接到台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偽造的」,以明明已經死去的母親的名義,來要我『志願當兵』的來信。(《我的抗日天命》,林歲德著,楊鴻儒譯,前衛,頁94)
除了以上這些不同的種種招募形式之外,據稱成為軍伕或者軍人,除了可得軍中的薪給外,家庭負擔的稅負可以減少,而各種配給可以增加,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是否就等於是一種強迫的方式?該影片的『懶人包』,竟然不知哀矜而要人們熱情的謳歌。。。
其二、是關於我島當年被轟炸的情況──
他說是盟軍飛機的「無差別轟炸」。。。
該影片中,使用照片說到有民宅、教堂與學校被無差別轟炸的情況。〈9分21秒~10分10秒〉
該片藉著強調有一家六兄弟姊妹,六人不同姓氏;其原因是他們的父母以為躲入教堂可能安全,沒想到被炸死;乃有六個遺孤,被六家人分別收養的慘事──然而,此處所強調的「無差別轟炸」,其史實究竟如何?知否,由於此事涉及戰後二二八悲劇問題,故特別更值得釐清。
根據當年我島被轟炸的紀錄中,我島民回憶中,明顯地有軍機故意避開民房的情況;以台北為例,根據當年的皇民醫師家庭,自稱最早的國語家庭;其父為辜顯榮先生的家庭醫生的林彥卿先生的回憶錄《無情的山地》稱,當年的實際是──
「台北大空襲……城內被轟得很慘……不僅對準軍事設施、政府機構,也針對台北市的日本人居住地區做選擇性的轟炸……翌日,我的朋友坐在開往北投的火車上,聽到有個日本人說:『昨天空襲太可怕了,只是被炸得全部都是日本人住的地區,台灣人住的一點也沒有受損』」。
這位林醫師還說到──
「終戰後有個傳聞說,五月三十一日的台北大空襲是由戰前台北一中的英語老師柯喬治所主導的,否則為什麼一個勁兒往日本人住地襲擊,台灣人住地能倖免於難呢?若從受害人地區推測的話,確實目標僅對準日本人地區。科喬治也曾經任教過台北高等學校,該校就沒有被炸。聽說是因為柯喬治曾被一中的日本人老師欺負,甚至毆打他,才心存報復。台北一中第三十八期的杜武豪,在美國加州當醫生,和柯喬治有來往。柯喬治告訴過他:『每次要攻擊台灣之前,在菲律賓的基地作行動說明時,都會拿出地圖指示不可轟炸到台灣人住地的大稻埕、萬華等地。』從美軍飛機選擇性的投擲炸彈這件事來看,日本人也多少聽到此風聲,可是他們解釋為這是美國挑撥離間內台人的手段,要使內台人反目成仇的緣故。當時,台灣總督安藤曾經說過假如美軍一旦登陸,台灣人究竟會站在哪一邊呢?著實帶來一點不安。」〈頁407~409〉
由上述的史料看來,那能算是「無差別轟炸」嗎?據稱,當年有些戰略物資是被藏匿到附近的自以為具有安全性的建築物,如學校或廟宇裡,以安藤總督言,自身就躲到新店附近的文山農場去了。
個人研究台灣史幾十年,覺得此事應該影響到柯喬治在他大作《被出賣的台灣》中,所稱我島民誤以為美國會願意為「託管台灣」而支持該悲劇事件之發生的前因。何以當年我島大都市中,不乏年輕人莽撞的一大理由。可惜過去論該事件者,從來無人關切,個人認為若要思患預防,不應過分簡單化,應該深入理解各方面。
筆者心中覺得此時此刻,可能正是我們社會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那完全沒有檢討東京當局的決策錯誤的論述,卻只是一味強調台灣總督府當年進行了哪些社會統制,其在當前的時局中之意義為何。。。
那強調地謳歌當年皇民化青年從軍的意義,其故意扭曲之真實意義為何?──很不幸的,該一扭曲不僅是我島上可敬的師大名嘴蔡正元老師的說法,也是美國學界的定調,而史實真相應該如前述所揭示,絕對是某種被迫下,才應徵成為志願兵的。
以上,是我不能不說的,不論新台灣史,不論舊台灣史,幾十年研究的認知;建議我的朋友們深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