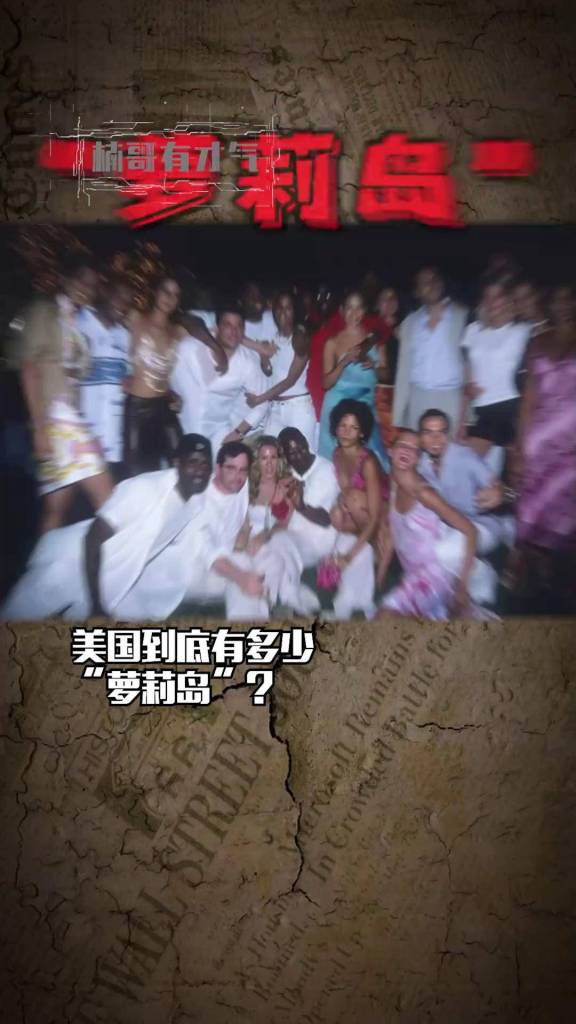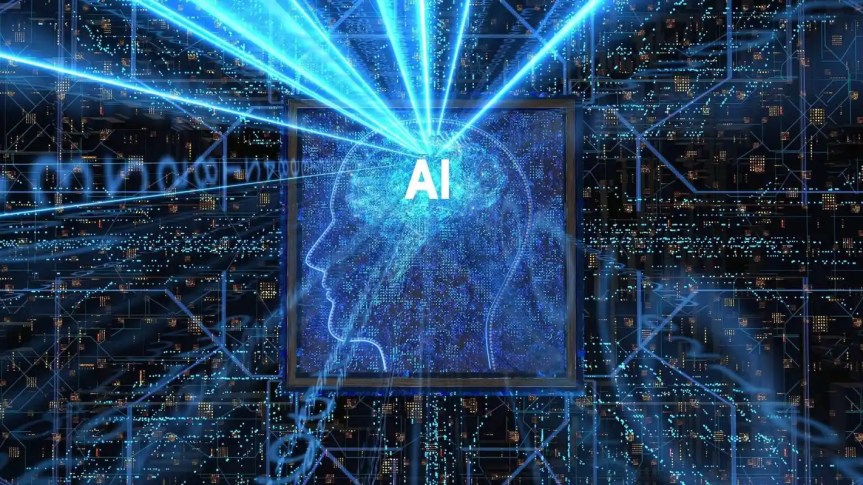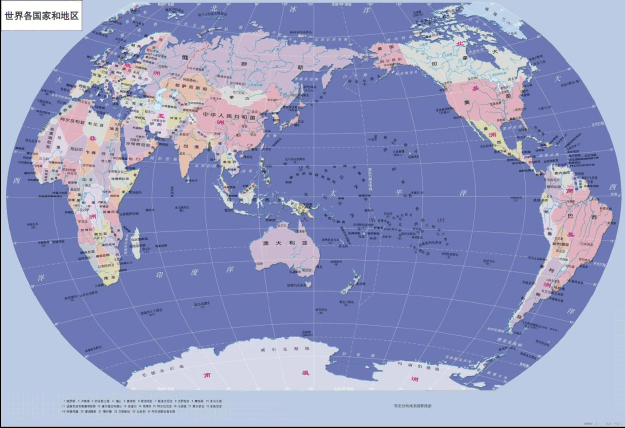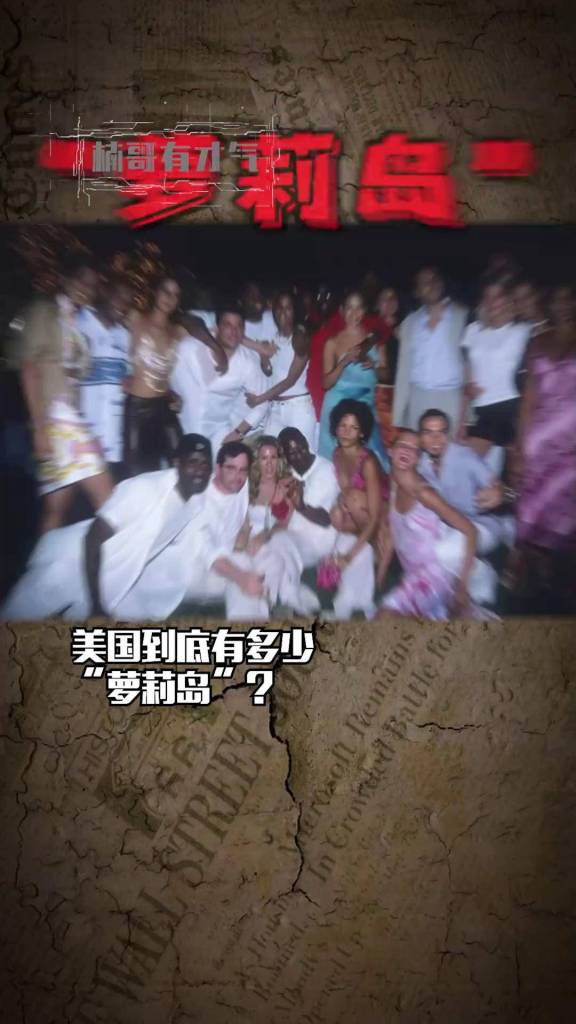愛潑斯坦的淫穢亂倫、金錢往來、無法無天的300萬件檔案公佈,雖然涉及川普的部份,悉數抹黑遮掩,但引起全球的轟動,不亞於2006 年澳洲人阿桑奇( Assange)建立的WikiLeaks ,一個跨國的揭密平台專門公開政府、軍事、企業等機構見不得人的機密文件。
英美道貌岸然的人物,至少包括美國政界的川普、克林頓、小布希、歐巴馬、安德魯王子,科技界的比爾蓋茲、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企業界的馬斯克、貝佐斯,都去過蘿莉島。
美國現任商業部長盧特尼克( Lutnick),曾於 2012 年在愛潑斯坦的蘿莉島上,與其共進午餐,並共同簽署合約投資一家科技公司(Adfin),他與愛潑斯坦有長期的商務往來及郵件聯繫;目前他正處於輿論風暴中心,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均有強烈呼聲要求他辭職下台。
美國前任商業部長雷蒙多(Raimondo),曾於 2012 年帶家人前往愛潑斯坦的蘿莉島,共進午餐。
美國前任財政部長薩默斯(Summers),他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及財政部長期間,與愛潑斯坦有密集的郵件往來與會面紀錄。
前英國駐美大使及商務大臣曼德森(Mandelson),他與愛潑斯坦關係密切,甚至在愛潑斯坦被判刑後仍維持聯繫;他目前正因文件涉及的內容接受調查,並已辭去相關職務。
英國的坎貝兒( Campbell),知名模特兒,她的名字出現在愛潑斯坦的私人聯絡簿小黑書及飛行紀錄中。
英國的傑格(Jagger),滾石樂團主唱,同樣出現在愛潑斯坦的私人通訊錄中。
英國的布蘭森(Branson),維珍航空公司集團創辦人,他曾邀請愛潑斯坦帶後宮來他的島嶼造訪;布蘭森事後聲明,僅限於商業場合接觸。
澳洲媒體大亨梅鐸(Murdoch)名字,出現在愛潑斯坦的小黑書聯絡簿中;愛潑斯坦的小黑書記錄了超過 1,700 名聯絡對象,其中包括多位媒體高層。
法國的布魯內爾(Jean-Luc Brunel)是法國知名模特兒經紀人,被控是愛潑斯坦的共犯,負責為其物色年輕女性;他在 2022 年於法國監獄中自盡。
義大利的卡普托(Caputo),義大利政治家,前歐洲議會議員,其姓名出現在愛潑斯坦的近期解密名單中。
西班牙的阿斯納爾(Aznar),前西班牙首相,文件紀錄了他與妻子曾收過愛潑斯坦寄送的包裹。
挪威前首相雅格蘭(Jagland)涉及愛潑斯坦的文件,其中有許多金錢往來,並已遭到挪威警方正式調查,罪名為嚴重貪腐,並要求挪威外交部撤銷雅格蘭的外交豁免權;挪威國會也因文件牽涉多名外交官與政治人物而啟動外部調查。
挪威的王儲妃梅特瑪麗特(Mette-Marit),她與愛潑斯坦在 2011 年至 2014 年間有上千次郵件往來,內容涉及度假行程與診所預約;她已對此公開致歉,並表示深感後悔。
斯洛伐克前外交部長萊恰克(Lajack),在文件中揭露他曾與愛潑斯坦討論美女及政治會面,而引咎辭去國家安全顧問職務。
日本的伊藤穰一(Joi Ito)曾任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主任,他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多次與愛潑斯坦接觸,並接受了愛潑斯坦為 MIT 提供的 52.5 萬美元捐款,以及為其個人投資基金提供的 120 萬美元,伊藤穰一曾邀請愛潑斯坦訪問 MIT;事件曝光後,已於 2019 年辭去 MIT 及多個基金會職務。
日本其他可能涉及的人士,及網路上流傳的一些日本名單,大多屬於商界名人,如索尼(Sony)或軟銀(SoftBank)的高管,但他們通常是曾經與愛潑斯坦有投資及企業的業務往來。
中國方面,首先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優秀非凡的女兒金刻羽,她的前男友Lawrence H. Summers(前哈佛大學校長,前財政部長)去過蘿莉島;加上她最近爆出投資失利的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3UZVRv0c0I)。
馬雲與一名女性合影,出現在一張編號 EFTA01612005 的照片中。
達賴喇嘛在愛潑斯坦電郵紀錄中顯示,愛潑斯坦一直試圖透過中間人(如麻省理工學院的 Joi Ito)聯繫達賴喇嘛,希望能在蘿莉島安排一次有趣的晚餐或會面。
柳傳志(聯想 Lenovo的老闆) 去過蘿莉島(僅為議論紛紛的傳說)。
美國涉及許許多多的政府官員,科技界、媒體界的領袖、精英,都去過蘿莉島,卻毫無道德檢討、法律懲處。美國社會只把愛潑斯坦案300多萬件檔案,當成社會花邊新聞,許多人深挖研究,作為茶餘飯後的笑料;這是美國道德的徹底淪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