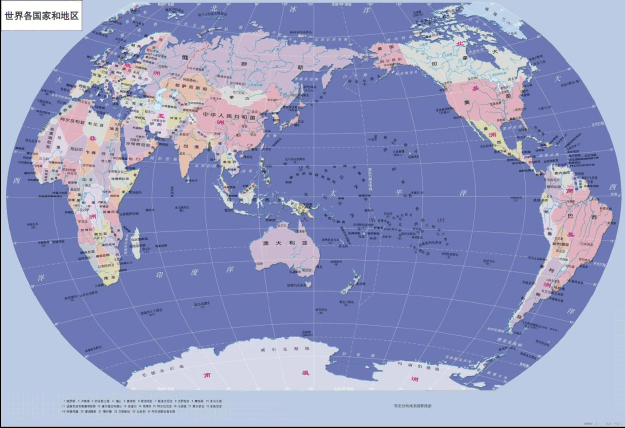《台游追紀》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江亢虎 於1935年出版的台灣遊記。
1. 批判殖民教育與漢文廢除
江亢虎最激烈的批評集中在文化侵蝕。他指出:
漢文衰落:他憂心日本政府推行的國語(日語)教育導致台灣青年逐漸遺忘母語與漢學傳統。
僑校受壓:他特別關注當時台灣的僑校教育,批評殖民政府透過教育體系限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
地位落差:他觀察到台灣人與日本人在社會地位、公職機會及薪資待遇上的極大不平等。
2. 外銷優先
大量優質的台灣米與砂糖被運往日本本土,台灣農民雖然辛勤耕作,自己卻往往只能吃番薯籤或劣質米。
專賣制度:日本總督府壟斷了鴉片、鹽、樟腦、菸酒等民生必需品的獲利,這些建設產出的財富絕大部分回流到日本國庫或日本企業手中。
3.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不對等
江亢虎觀察到,儘管日本設立了學校,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完全不對等:
階級限制:台灣子弟多數只能就讀「公學校」,而日本人則就讀設備較好的「小學校」。
升學天花板:台灣人很難進入法律、政治等核心治理領域,多被引導至醫學或農業等實務領域,目的是為了培養便於殖民統治的工具人,而非真正的領導人才。
有建設無權利:台灣人即便具備高學歷,也難以在總督府中擔任高層職位。這種「有形的現代建設」掩蓋了「無形的政治奴役」,台灣人被排除在決策圈外,無法決定自己家園的未來。
4. 建設品質的「虛有其表」
江亢虎在書中提到,日本的建設往往追求表面上的統一與觀瞻,但缺乏實質的精細度。他觀察到:
材料與質感:
相較於他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古蹟或精細建築,他認為台灣的殖民建築(如某些公家機關或宿舍)顯得單調且缺乏文化底蘊,甚至有一種「臨時性」的感覺,像是為了統治而快速搭建的「盆景」。
設施的「區域失衡」:
他指出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極度不完善,因為其分佈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功利性:
城鄉落差極大:所有的現代化建設(電力、自來水、洋樓)幾乎都集中在日本人居住的區域或大都市中心。
廣大農村的荒廢:廣大的農村地帶除了與糖業、林業相關的運輸系統外,基礎設施極其簡陋,品質與大都市天差地遠。這證明了日本並非真心要建設台灣,而是只建設對殖民掠奪有利的「孤島」。
與「滿洲(東北)」的強烈對比:
江亢虎當時已觀察到日本對「滿洲」的投資力道遠勝台灣。
建設規格低落:他認為日本在台灣的鐵路多為窄軌,車廂狹小,與日本在東北打造的高規格準軌鐵路和現代化重工業體系相比,台灣的建設顯得規模狹小且「品質次一等」。
功能單一:他批評台灣的建設品質被侷限在「農業供應」層次,缺乏能讓地方長期繁榮的重工業與科技研發基礎。
江亢虎特別批評教育設施的品質。雖然有公學校,但設備與師資遠遜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這種「不完善」的教育體系,在他眼裡是故意將台灣人的智識品質壓制在低水平,以維持穩定的勞動力供應
5. 城市規模與氣度(氣象)的落差
「盆景」與「大都」之別:江亢虎認為當時的台北雖然整潔,但與上海、南京等具備國際規格的現代大都市相比,顯得格局狹小、氣象侷促。他在書中描述台灣的城市更像是「殖民地的樣板」,缺乏像近代上海那種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文化深度。
建設品質的「廉價感」:江亢虎觀察到日本在台的公共建築雖然整齊,但相較於上海租界或南京國民政府推動的「首都計劃」中那種宏偉的、結合東西方美學的永久性建築,台灣的建設顯得較為單一、功利,且多為因應統治需求的「次級品」。
6. 工業規格的「次等化」
窄軌 vs 準軌:當時台灣的鐵路系統多採用「窄軌」,這在江亢虎等文人眼中,是技術與規格上的落後。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大陸的主要幹線及日本在東北(滿洲)建設的鐵路多為「標準軌」,規格更高、運載力更強。
重工業缺失:日本對台灣的定位是「農業台灣」,因此建設集中在糖廠、水利等民生輕工業。而當時中國大陸大城市(如武漢、瀋陽)已有較具規模的鋼鐵與機械工業,江亢虎認為台灣的建設缺乏長遠的產業主體性。
文化建設的貧乏:江亢虎強烈批評日本在台建設「重物輕人」。雖然有硬體設施,但缺乏像北大、清華或中大那種具備深厚學術自由與人文底蘊的最高學府。他認為這種「閹割版」的建設品質,是導致台灣文化建設、漢學傳統與現代學術不如大陸都市的核心原因。
7. 識字率的真相:不具深度的「工具人教育」
數據假象:日本宣稱的識字率,大多是指能聽懂簡單日語指令、書寫假名的程度。江亢虎批評這種教育是「斷根教育」,台灣人雖然「識字」(日文字),卻失去了閱讀漢文古籍、傳承民族文化的能力。
品質低下:公學校的課程以勞作、簡易計算與日語為主,缺乏科學精神與人文思想。這種「低標識字率」只是為了方便日本工廠管理台灣勞工,與當時中國大陸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發展出的高等學術與全才教育相比,品質極其低劣。
8. 公共衛生的真相:為了「殖民者」而建設。
防疫大於醫療:日本在台推廣公共衛生(如滅鼠、防治瘧疾),核心動機是擔心傳染病會波及來台的日本官員與軍隊,並確保台灣勞動力不會因為瘟疫而崩潰。
資源分配極端不均:
硬體落差:現代化的自來水、排水系統主要覆蓋在日本人聚居的「城內」或「新市鎮」。
醫療門檻:雖然有醫院,但高昂的費用與文化隔閡,讓廣大底層台灣農民生病時仍只能依賴傳統草藥或神明。江亢虎觀察到,台灣民眾在衛生觀念上並未真正「現代化」,而是被動地活在殖民政令的管制下。
9. 與中國大陸城市的對比
缺乏尖端實力:當時上海的雷士德醫學研究院等機構,其醫療研究水準是國際級的。相比之下,台灣的公共衛生僅停留在基礎的環境清理,缺乏深度的醫學研究與國民體質的全面提升。
社會素質的斷層:江亢虎認為,大陸大都市的現代化是自發的、與文化並行的;而台灣的現代化是被強加的、品質低劣的,這導致台灣人在表面整潔下,內在的知識體系卻是破碎的。
江亢虎在遊歷後曾流露出,台灣像是一個被精心管理但毫無生氣的「模範農場」,而朝鮮與東北更像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次帝國中心」。這種「建設不完善」的本質,是因為日本從未打算在台灣建立長久的工業基礎,只是想榨取其農業剩餘。
事實證明:直到二戰末期因應南進政策,日本才開始在台灣發展輕金屬等工業,但那時的技術規格與朝鮮、滿洲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