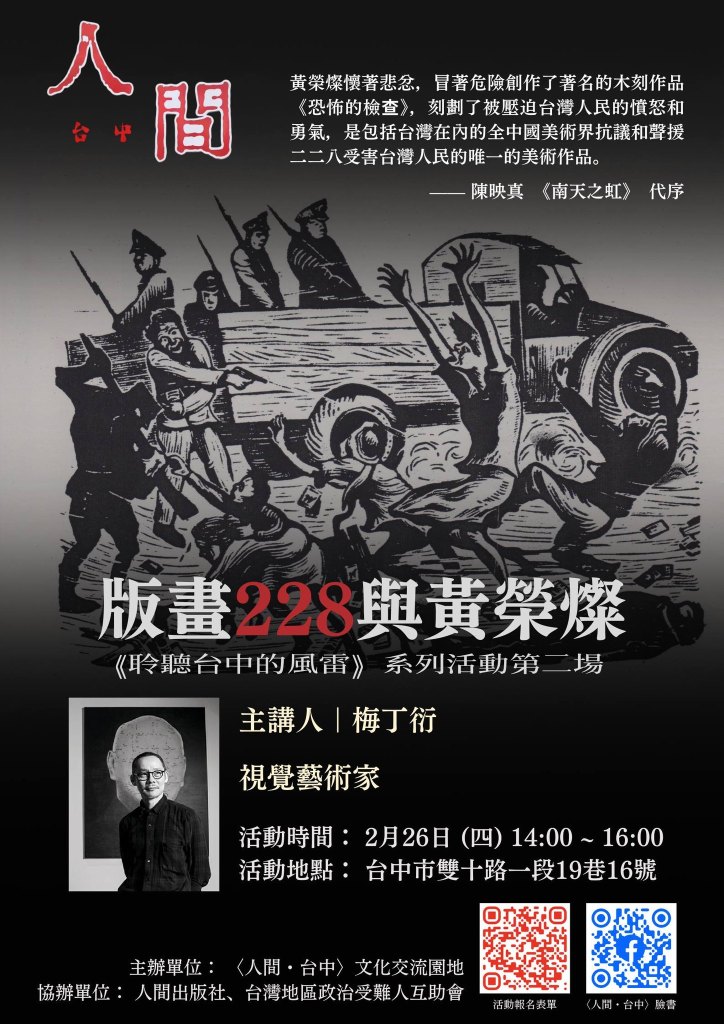晨起閱報,說是總統在出席大陸台商春節活動致詞時,多次以「中國大陸」,而不是慣用的「中國」來稱呼對岸,並明確釋出希望兩岸交流合作,和平共榮的意願;許多媒體報導都指出這樣的說法表現了很大的善意。
那麼中國跟中國大陸到底有何不同?
首先,「中國」一詞在在語意上是一個整體性指稱(totalizing reference),意指將所有現象、經驗或知識納入單一、統一的框架或解釋系統中;因此,當稱呼對岸為「中國」時,其預設的意義就是,對岸是一個主權完整、邊界確定、政治統一的國家實體。
說白了就是,「中國」是一個不包含我台灣在內的政治實體。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則是部分指稱(partial reference),其中的「大陸」是地理修飾語,指的是中國除了大陸之外,還可以有其他的部分,可以是新疆,可以是西藏,當然也可以是台灣。
易言之,「中國大陸」只是「中國」這個政治實體的若干區域之一而已,而此,就出現了緩衝的空間。
所謂的善意出自於此。
再說明白些,使用「中國」一詞,等同於啟動「我國跟他國」的關係結構;使用「中國大陸」則刻意地避免了這種明確的劃分,等同於是策略性的模糊了對主權的預設。
這當然可以理解為一種「策略性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而這種模糊並非語言的不精確,而是一種刻意維持的語用空間;說話者既不直接指稱對岸為完全的外國,也不明言兩岸同屬一國。
因此,「中國大陸」一詞的使用就是對主權問題在語言上的迴避,讓兩岸關係處於未明確分類的狀態,而這種未分類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政治立場,使政治立場保持可調整性。
平心而論,執政黨避之唯恐不及的「九二共識」就是這種刻意維持模糊的產物,無論是當年國民黨強調的「一中各表」,或是對岸堅持的「各表一中」,其實都提供了讓大家各說各話,卻又不至於僵持不下,可以共同發展的空間。
這麼好用的東西卻棄之如敝屣,真是可惜了。
不過,如果就此就認為執政黨要走回「九二共識」的老路子,可能又有點盲目樂觀了;畢竟把對岸視為他國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年輕一代。
記得多年前,劉杯杯曾經參加一場媒體主辦的座談,當時以個人經驗舉例,說是周遭有年輕人每每稱呼赴大陸為出國,並不是很恰當;結果此一說法,遭了小小的網暴,多人留言質疑,去大陸當然就是出國啊,不然哩?
這邏輯其實是相同的。
「出國」的語義是明確的,就是以國界區隔,去到了另一個國家;而「去大陸」就沒有離開國家的意涵,就只是轉換一個地理空間而已,還是在國境之內。
總之,願意稱呼對岸為「中國大陸」,就是一個進步,至於能夠走多遠?
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