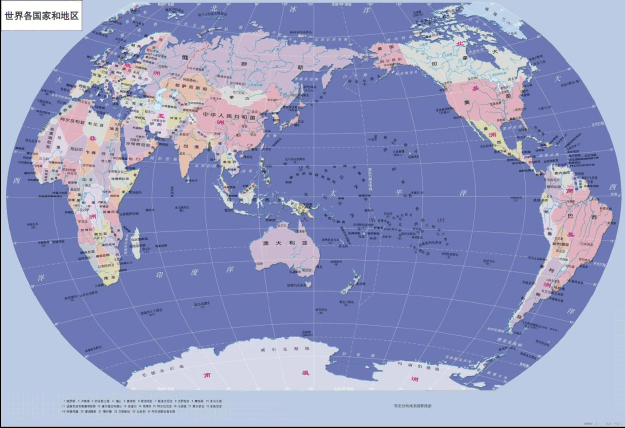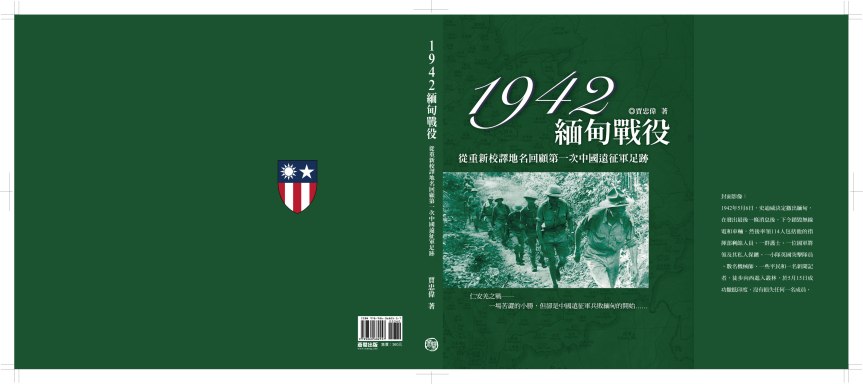海外(含台灣)的愛國人士都反台獨、愛中國,但其中有不少人覺得習近平很糟,覺得大陸經濟不行,社會危機重重,政治在崩潰的邊緣。與台獨和反賊不同的是,他們憂心忡忡(而非幸災樂禍),但對現實的認知卻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認知是從那裡來的?顯然不是從反賊或台獨的宣傳來的,因為他們也討厭台獨與反賊。他們如此認知,多半是他們在中國國內的朋友告訴他們的。而他們的朋友又是誰?多半是大學教授、中級政府官員、成功商人等。總之,就是他們這幾十年來所來往的政商名流、社會精英。簡而言之,就是他們的朋友圈,異口同聲,使他們相信這是大陸真實的狀況。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點,他們的這些朋友,都是習近平反腐打貪的受害者。
中級政府官員,不用說,恨死習近平了。不但難以貪污受賄,就連灰色收入都沒有了。雖然加了薪,但那一點點「養廉銀」,杯水車薪,根本就是個笑話。但他們總不能說「習打貪太壞了」吧?只好拐彎抹角找各種理由說習的壞話,包括「小學生」之類的。
與之相同的是中間等級的商人。以前與官員勾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營商環境更公平了,但問題是,他們是「不公平」的受益者啊!他們喜歡這個「公平」嗎?這不是很容易理解嗎?
最後,就是知識分子。問都不用問,知識分子(教授、記者、文藝工作者等等)肯定都討厭習。坦白說,如果我生活在大陸,在大陸的大學教書,說不定我也討厭習,因為習收緊了言論尺度。但你想想,習為何這麼做?那還不是因為反腐!反腐真的太難了,這點就不多說了,不明白的人,我只能說你歷史書讀得太少。反「反腐」的力量無比強大,而他們當然不會明目張膽說「我要腐」,而是利用反腐輿論來個「把水攪渾」。也就是漫天造謠,破壞反腐節奏,讓你疲於奔命,讓民眾真假莫辨。為了對付這群人,只好「管制言論」。那麼首先受傷的,就是知識分子。(當然,應該管得更細緻,而不是「一刀切」;但這說來容易做來難。)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這三類人,他們怎麼可能有習的好話?
那麼,該怎麼判斷大陸經濟好不好呢?當然,不是很好,但與世界各國相比,也不是很壞,遠遠沒有到要造反,要改朝換代的地步。
首先看各種數字,GDP、股市、進出口、採購經理人指數、還有「李克強指數」等,以及基尼係數,綜合判斷,就知道經濟不算太差。房價當然是個大問題,在高點買房的人,我不相信他們不恨習近平。但你有統計過房價平穩的城市與腰折或六、七折的城市各有多少嗎?新聞只會報後者,不會報前者。你要實地探訪,或閱讀真正可靠的研究分析資料,才能得知實情。只看新聞,會有以偏概全的偏差。
有人透過在大陸搭計程車的經驗來看大陸經濟。但計程車、網約車司機一旦知道你是海外來的,那肯定對習也沒好話,因為他們知道要迎合客人的胃口。但你不但要聽他們抱怨的是什麼,還要自己去想有什麼是他們沒抱怨的。後者也同樣重要,卻是很難抓到的部分。
要知道,學生很少不罵老師的,因為罵老師可以顯示學生的厲害,當乖乖牌豈不是太沒有意思了?但學生罵老師,就真的代表這老師不好?你得會聽,自動補足他沒有說的部分。之前有學生在網路上罵我,說我的考題居然考「某某詩句是出現在課本的第幾頁?」你看了是不是覺得這個出題老師簡直是個神經病?但學生沒有告訴你的是,我的考試是開書考試,沒帶課本的還允許借。有課本在手,這樣的題目就是再簡單不過的送分題;但就是有人連某某詩在課本何處都找不到,故而上網罵我。
過去貪腐盛行,但經濟高速發展,錢好賺,人人充滿希望;現在經濟發展趨於平穩,錢不怎麼好賺了,人們自然易有怨言。但如果再加上貪腐情況和過去一樣,那局面會如何?你想過嗎?而經濟發展趨於平緩,是因為習打貪之故?還是說,經濟在高增長之後必然趨向平緩,而習的打貪是及早化解了一場大危機?你認為哪個對?(當然,還有打房的問題。習打房對不對,這是更難討論的問題;但不論如何,你都不能說他犯了幼稚的低級錯誤。)
道隱於無名。老子說,反者道之動;應於無聲之處聽驚雷。在看得見的枝枝葉葉上品頭論足,已落入下乘。更何況,追本溯源都接錯了線,尋錯了根脈,那判斷就完全失準了。
中央軍委從七人變到只剩二人,這是習權力穩固還是不穩固?智者自知,就不再討論了。當然,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含藏危機,這也是肯定的。唯此中因果,不能顛倒。
個人淺見,在習任上,中國應是穩定向好發展的局面,應無疑問。比較有疑慮的,還是「接班」問題。習在此問題上是否有所「制度創新」?此事還在未定之天。若能有一個制度性的設計,並且能平穩運行,則其功當不在「國家統一」之下。畢竟全世界古往今來的「非民選」制度中,都還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至於言論自由云云,我想只要反腐取得階段性成果,在習卸任的前後,一定會放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