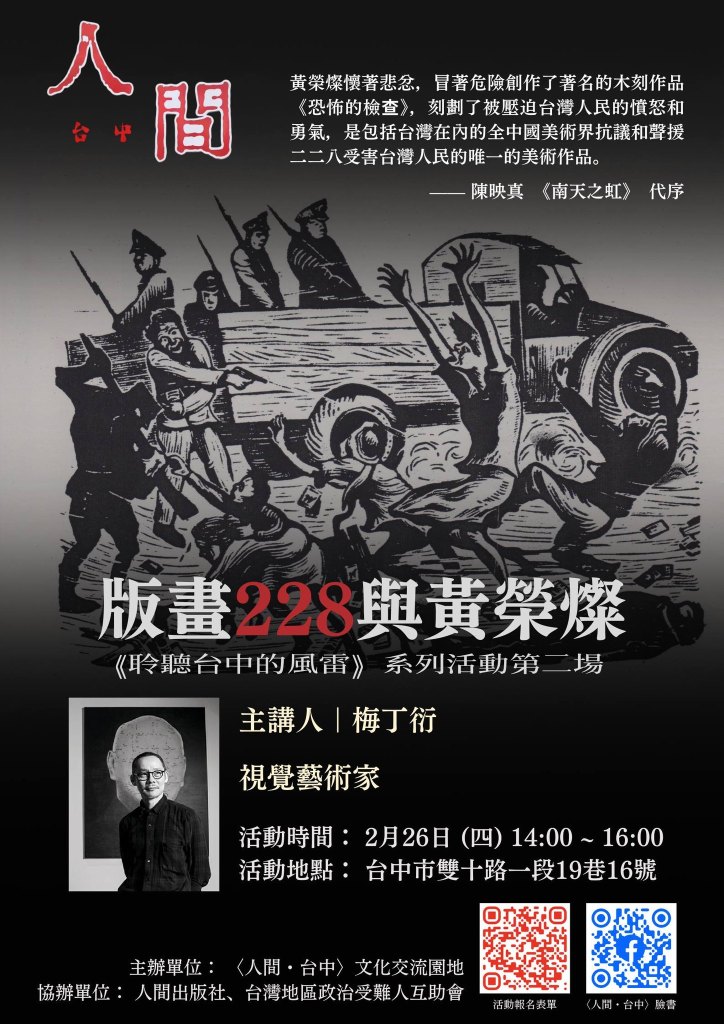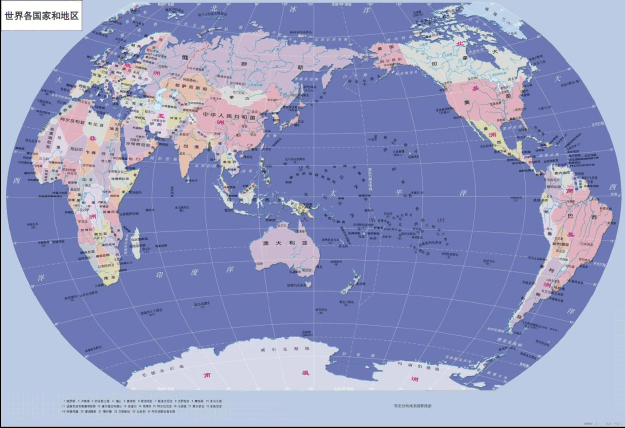1987年反共戒嚴令解除。在此前後,伴隨著澎湃洶湧的政治、社會運動,台灣民眾才敢打破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禁忌,針對228事件與50年代白色恐怖,展開重新尋回被湮滅的歷史記憶的運動。
二戰結束後中國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的繫獄倖存者也在林書揚等人串連推動下成立了最早的政治犯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是,因為長期的嚴密監控,多數成員幾乎都是「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時期總動員法」罪名下服刑的政治犯或其家族,潛在的警戒心理仍未全消,所以仍然在章程中十分慎重含蓄地以「共同認識」(而不敢用「行動綱領」的條目)泛泛地表示:「促進中國統一,台灣自治,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信條。然而,面對國家安全法的反共基本國策、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反中脫中的分離運動,以及朝野勢力共塑的反共民意結構等三大因素制約,該會的活動多以維繫會員聯絡和生活互助為目標。
1988年,李登輝在兩代強人長期主斷國事所造成的混亂殘局中登上執政黨主席和台北國府元首的職位。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並以「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取捨原則」頒布特赦復權令,在衆多受害者之間,僅對具有「造勢效果」與「宣傳意義」的少數「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採取特赦;對其餘數十年來在惡法苛政下的上千犧牲者,則因其「無爲我用」或「弱勢無用」而棄之不顧。就其内容來看,這份特赦名單其實只是作為他與在野黨進行「政治交易」的一張「政治犯牌」而已。
5月30日,「跨黨派立委七人小組」在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行一場名爲「特赦及減刑」的公聽會。一九五〇年代曾經在懲治叛亂條例的羅織下被判入獄,經歷過鐵窗歲月數年、十數年、數十年,而倖存於世的所謂叛亂犯出獄者,以互助會會長林書揚為代表,公開質疑此一特赦令。他們指稱,特赦復權令認為「二二八事變中民衆在槍林彈雨中的自衛行爲,或一九五O年代軍法大審時期的上萬蒙難者對國家統一和社會正義的深切企盼」,「屬於永無可赦的罪」;這種「心態不能不説是一種嚴重的階級歧視,甚至近乎法西斯的理念立場。」據此,他們向李登輝提出三條建議:
一、凡所有政治犯不分黨派或有無黨派一律特赦復權,包括工作權。
二、在動員戡亂時期未正式宣布終止以前,應先行凍結國安法第二條全條,不可僅廢除其中有關主張分裂國土之一段。
三、凡在軍法、司法審判中所造成的所有冤案錯案、假案,一律平反。
1991年,台灣當局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邏輯上不再視中共為國內叛亂團體,實質上卻是為了將大陸地區外部化、「敵國化」的法理準備。也就是說,它既是島內民主化進程的必然,更是「切斷兩岸過渡性和連結性的信號」。
1992年,李登輝為了拋棄歷史包袱,也為了拉攏在野黨,終於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向228受難家屬致歉,並成立中央跨部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與「二二八賠償辦法」,開始辦理補償等等事宜。然而,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雙戰架構下產生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卻沒有受到台灣社會官方與民間的相對重視,而遭受「階級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