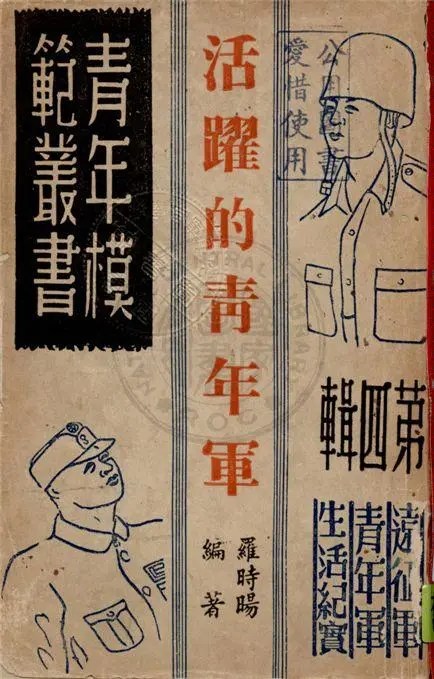將近入睡的時刻,房子裡突然響起了電話鈴聲。
他來美國還不滿半年的時間,從來沒有人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他。
他拿起話筒來,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聲音,更添增了他緊張的情緒。
「請問周武昌先生在嗎?」他聽到對方這麼詢問。
他說,他就是周武昌。
「真不好意思突然打電話給你。」對方說他的名字是蔡仲庚,匹茲堡大學中國同學會會長。「今天我從外國學生顧問那裡得知一個不好的消息。我們學校新來的同學胡玲玉不知什麼原因吞食了起碼半瓶的安眠藥。沒有人曉得她怎麼弄來那麼多的藥丸。下午我陪同顧問去胡玲玉的研究室開啟了她的書桌抽屜──在平常的狀況我們是不能這麼做的,可是這是特殊的狀況──總之,我們在那裡找到了幾封來信,其中有一封是你寄給她的。冒昧想確定一下,胡玲玉是你的朋友吧?」
他說,他和胡玲玉是小學同校但不同班的同學,在大學則是同校但不同系的同學。他接著說,也許他可以猜想一兩個為什麼她會這麼做的原因,但他並不真的那麼瞭解她。
「噢,請不要誤會,我不是來打探消息的。我打電話給你,是想求求你幫我們一個忙。」
他說,如果他幫得上任何的忙──
「說實在話,我們已經束手無策了。」蔡仲庚不等他講完就繼續說:「我問過今年剛到學校的留學生。沒有人認得胡玲玉,也沒有人有機會與她交往。」
他的腦子閃過第一次看到胡玲玉的樣子。那時他剛從南部轉學到北部去。他的同學指著她的背影告訴他:「這就是一班的玉皇大帝,沒有人考試考得過她。如果不相信,你可以轉到一班去,看看你能不能考贏她。」他回說,為什麼他要轉去一班?「只是想跟你說,沒有人不怕她,也沒有人太喜歡她。」這時候,他看到胡玲玉轉過身子走進一班的教室去。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看到她紮著馬尾巴的辮子,還有她白晰的臉孔,上面帶著一種似乎相當滿意自己的神情,但不是那種看了會讓人感到畏懼的神情,他覺得。然而他很高興沒有被分派到一班去。他還在南部的時候就聽人說,北部有一些好學生真不是蓋的,任你怎麼拼也拼不過他們,沒想到他在這裡碰到的居然是一個女生。
當他掛上電話,妻子問他是什麼人打來的。他嘆了一口氣說,有人從鋼鐵城打電話給他,問他能不能過去慰問在那裡尋短見的一位女同學。然而他說,他並沒有立即答應對方,只說會看看有沒有辦法在一兩天內趕過去。妻子的回應卻讓他感到意外。她說,一個人在美國做出這樣的事,卻沒有任何親人在身邊照應,蠻叫人同情的。他問妻子,可以陪他一起過去嗎?妻子說:「可以呀。但如果你想自己一個人去,我也不反對。」他回說:「妳開什麼玩笑。」
第二天,當他坐在辦公室裡,突然失去了前往匹茲堡的想望。他坐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一面聽同樣是助理的高年級研究生以老練的聲調為學生解釋習題解答。他聽到他們直接呼喚學生的名字,顯示這些學生已經出入這個辦公室好多次。他自己從來沒有任何學生前來求助兩次以上。如果不是他在班上的課業不比其他同學差,他會擔心自己很快就失去這個工作。
他打開幾乎空無一物的抽屜,想到胡玲玉的抽屜裡竟然存放著他寫的信。出國以前,他在留學生講習會上碰到了胡玲玉。那天她顯得神采奕奕,主動跟他打招呼,並且問他要去哪個學校,接著她把自己要去的學校告訴了他。「鋼鐵城並不是頂尖的學校。」胡玲玉說:「可是在美國的第一年你不能期望立刻上最好的學校。我到了那裡還會繼續努力。」她沒有說她會繼續努力什麼,卻囑咐他到了美國以後寫封信給她。「信寄到我的系裡就好。我還是同一個系,不像你改了行,變成理科學生,乖乖隆地咚!」
他感覺她只是在嘲諷他,但到了美國以後仍然寫了封信給她,把自己的地址和電話都附在信上。然而隔了好一段時日,他都沒有收到她的回信。現在他開始感到好奇,除了他以外,還有什麼人曾經寫信給她?為什麼蔡仲庚不跟那些人聯絡,卻找上了一個並沒有收到她回信的人?
中午的時候,他獨自坐在活動中心外面的陽台上,開始吃妻子為他準備的三明治,同時看著剛下課的大學生從前面的廣場穿梭而過。看到這些充滿了活力的學生會帶給他一點雀躍的感覺,讓他暫時忘記自己不明確的未來。妻子說,她今天中午要跟一位系主任面談,看看是否能在他們的系裡旁聽一兩門課。她本來在華府的一間大學獲得了獎學金,到了那兒卻發現學校並不提供宿舍,當地的生活費又高得嚇人。他沒有責怪她變得那麼消極。自從在國內遭逢一樁政治事件,他和妻子都覺得他們原先就讀的學科已經沒有任何前景可言。他囑咐她搬過來與他同住,看看這裡有什麼其他出路可尋。考慮幾天以後,妻子答應了他。現在他們兩個人共用他的助教獎學金,勉強還能過活。至於未來會出現什麼問題,特別是財務方面的問題,他已經懂得先將它們置諸腦後。
他看到兩個大學生向廣場跑去。一個人很快停下來,另一個人則跑到廣場的另一邊,然後回轉身來,把手裡的飛盤扔擲給前一個人。就這樣,飛盤從這兩人的手中飛出又飛回,好像從來不做其他的思慮。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也是個充滿活力的學生。他在文學院的迎新會上遇到了胡玲玉。那是晚間的時候,在二樓的一間大型教室裡布置了一些彩帶、彩球與壁報,還放置了一些數目不算多的小點心,任由還有機會看到它們的人取用。那天出席的老師與學生很多,人群很快擴散到教室外。從面對草坪的窗口,他還可以看到另一邊的走廊也聚集著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站在點亮了燈的辦公室外面。他準備離去的時候,胡玲玉走到他的身邊。
「真不簡單,會在這裡看到你。」她說:「如果你不是文學院的學生,我就不想繼續跟你講話了。」他說,他確實是文學院的學生,而且早在聯考的放榜單上看到她也在同一個院裡。她點了點頭,繼續說:「我對理工科就是沒任何好感。太多人想擠進那些科系去。我覺得我們社會缺少的其實是能夠為文化奉獻心力的人。」
當人群顯得稀疏的時候,胡玲玉問他願不願意陪她走回宿舍去。走出了文學院大門,胡玲玉向他解釋,她的父親在那年暑假去世了。她母親帶著妹妹和小弟搬去台中暫住在舅舅家,這是為什麼她不得不住進學校的宿舍裡。
這是他第一次走在晚上的校園裡。位於不遠的活動中心傳來了練習吹喇叭的聲音。相同但不完整的曲調一遍又一遍地傳過來,似乎在考驗人們對音樂的忍耐力。他們很快走到胡玲玉的宿舍,團團圍繞著這建築的高牆提升了外人對它的想像力。「假日早上還有好多男生站在這裡排隊呢。」胡玲玉說:「下次你再來的時候就曉得要站在哪裡了。」他回說,他並不認識這裡的任何人。「你認得我呀!」她顯得有點不高興地往大門走去。
如果妻子詢問他,他會說那是他跟胡玲玉僅有的一次交往。事情也確實如此。而且,他不需要跟她交往就能夠聽到她的林林總總。現在人們談論的不是她的成績,而是她的才智。「她可以在幾天裡讀完別人一整學期才讀得完的資料。在討論會上,她還能揪出別人論點的疏失,讓說話人當場下不了台。」他開始感覺自己並不是她旗鼓相當的對象。尤其當他跟一個剛要好的女孩走在一起,偶爾看到她從走廊的另一端迎面走過來,臉上帶著一種他以前所不熟悉的表情。一種畏懼的感覺會突然跑進他的心裡,就像他的小學同學所感覺的那樣。
那天回家時,妻子在車上告訴他,她約談的系主任說,她不需要同意就可以去旁聽她感興趣的課程。然而去聽課以前,她最好知會授課的老師一聲。妻子覺得自己做了一項突破,他也樂於相信如此。他問妻子,還想不想去鋼鐵城,把不愉快的事暫時拋諸腦後。妻子說,她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但只要他想去,她願意奉陪。
晚上,他撥了一通電話給蔡仲庚。對方聽到他隔日就能趕過去,感到非常欣慰。如同上次一樣,蔡仲庚不等他把話講完,就急著把新得來的消息灌輸給他。蔡仲庚說,他們的學生顧問看到胡玲玉的抽屜有一兩封信來自加州大學的一位教授的來信,就主動打電話給他。然而那位教授說,他與胡玲玉討論的是她申請入學的事情,詳情他不能對第三人透露,而且很快就掛上電話。
他的腦際突然劃過一道火花,立即問蔡仲庚那位教授的名字。蔡說,學生顧問並沒有告訴他太多細節。他又說,醫院的護士告訴他,胡玲玉吞下的安眠藥其實不足以致命,可見那是她在一時衝動所做的事。「我把這些資訊告訴你,是要讓你知道,有老朋友來看她一定能夠幫忙她回復正常的情緒。」
掛了電話以後,他突然感到非常氣憤。他把自己聽到的話轉告給妻子。「為什麼別人都袖手旁觀,我們卻要老遠趕去那裡?當年我們系裡發生事情的時候,有人來慰問我們一聲嗎?妳被拔除助教職位的時候,有人為妳說過一句話嗎?」妻子沒有回答他。她可能不願意回想傷心的往事,或者不覺得他們的遭遇可以與胡玲玉的情況混為一談。
他計畫在第二天下午上完課以後,就直接開車去鋼鐵城。他與妻子約好在學校對面的A&P超市會面,在那裡他們可以購買一些食物放置到車上。站在A&P的付費隊伍上,他想起高三放春假以前,班上同學發動了一個自行車之旅,目標是環繞北海一周。「旅行回來我們就要好好讀書,準備大學聯考了。」他們這樣交代自己的行為。現在他覺得自己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當車子駛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Raleigh),他開始覺得即使在匆忙中跑這麼一趟行程也是值得的。起先他們在路上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景觀。等到這條公路合併到I-95以後,城市的景象出現在路的兩旁。大型的廣告牌豎立在路邊的空地上,一排排的房舍躲在稀疏的針葉林背後,偶爾還有高聳的建築物站在坡地上,像是在監視公路上來往的車輛。到了Richmond,他感覺他們的公路彷彿從半空中切入這個城市,把已經點了燈的街道甩到它的下方。這樣的景象讓他感覺,這可是第一次他開進了他以前所認識的美國。
然而城市的景象很快又讓位給單調的景觀。過了好一陣子,華府的名字才出現在看板上。他以為他們起碼可以在那兒看到以前在照片上看過的畫面,然而他們的車子很早就駛離I-95,轉入城西的環城公路。他不再看到燈光照射的廣告牌或閃爍著燈火的建築物。路上的車輛也逐漸在減少,四周變成一片漆黑,他不敢貿然從任何出口駛出公路去,這讓他打算停歇在華府吃晚飯的想法落了空。然而妻子說不要緊,車上還有足夠的食物。其實他並不感覺餓。在那次北海一周的旅行中他也不感到餓。中午休息時,他們把腳踏車推到海灘上,那裡一個人也沒有。冬季的臺灣海峽卻不平靜,凶猛的波浪不停地拍打黑色的礁岩,發出嚇人的聲音。有同學從袋子裡掏出事先為大家準備的零食,但他並沒有接過食物。
當賓夕法尼亞的名字與州徽出現在看板上,他知道他們已經駛離人口稠密的區域。收音機裡播出的鄉村歌曲開始逐漸減弱,最後完全被「絲、絲、絲」的聲音所取代。他想告訴妻子,他已經找不到任何電台,卻發現她已經睡著了。現在他們的處境跟那時的北海之旅越來越相似:即使想走回頭路也不比繼續向前行來得划算。他記得,當他們快接近基隆的時候,天開始下起雨來,這是沒有人事先料想到的情況。每個人只能自顧自地繼續往前騎,期望目的地很快出現在不遠的前方。騎到一段下坡路的時候,有人呼喊他的煞車不靈了。其他的人只能建議他用推車方式往前走。不久,所有的人都改用這種方式繼續往前走。
他們已經在這條公路上行駛了好長一段時間。鋼鐵城的名字終於出現在高速公路的看板上。他實際上所看到的字眼並不是鋼鐵城,而是匹茲堡。然而當他提醒妻子自己的發現時,卻使用了「鋼鐵城」這個名字。他找到一個休息區把車子停下來。蔡仲庚囑咐他快接近匹茲堡的時候打個電話給他。接電話的人正是蔡仲庚,顯示他還在電話旁邊等待。他要他們轉到279號公路以後再打一個電話給他,他會開車去那裡與他們會合。他回到車子裡,查詢一下地圖,發現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距離279還很遠,不懂蔡仲庚為什麼要他們去那裡跟他會合。
他們重新上了路。妻子睡過以後恢復了精神。她開始跟他講話,企圖讓他保持清醒。妻子說,她已經想過,回去以後會設法在當地找個工作。這個想法驚醒了他。他反問妻子有沒有想到這會帶給她的風險。妻子說,她當然想過。然而如果她想繼續求學,勢必要給自己賺足學費。現在他明白妻子一直在思慮的是這個問題。但他只回答,等他們回去以後再慢慢商量。
前往279公路花去了他們很長的時間,蔡仲庚卻講得好像他們很快就可以到達。看板上終於出現這個公路的號碼。他轉入了這條路,感覺他們已經開進匹茲堡的市區範圍。他在一個看似酒店的馬路對面停下了車子。他期望走進店裡去,在那兒坐下來,吃點東西,等待蔡仲庚來跟他們會合。然而他開了門以後看到的只是一個即將打烊的店鋪。更令他失望的是,沒有人出來接待他,他也找不到公用電話。
重新回到馬路上,他在不遠的地方找到一個電話亭。蔡仲庚一接到電話就問:「怎麼會這麼久,是不是找路有困難?」他聽到這話,感到更加光火:「我們原來已經很接近匹茲堡的東邊。為什麼你要我們繞那麼遠的路到西邊來?」蔡仲庚停頓了一下才回答:「你們從東邊來?」當然啦,他說。「唉呀,我真該死。我一直以為你們住的地方在我們西邊。」蔡仲庚問清楚了他們的所在,說他立刻開車去會他們。
他掛了電話,看看手錶,發現時間已經是半夜一點多鐘。就在他跨過馬路的時候,覺得有東西飄落到自己的頭上。他抬起頭來,發現天上竟然飄下了雪花來。在路燈裡遊盪的雪花看起來特別顯眼,這帶給他一種莫名的興奮。原來匹茲堡的深夜會飄雪,卻沒有任何人注意到,即使是開車經過這裡的人。然而當他走回自己的車裡,雪花已經消失了。這似乎只是瞬間發生的事情,他沒有告訴妻子自己的發現。
蔡仲庚的車子很快出現在馬路上。他一打開車門就發出長串的道歉聲,並且要他們跟著他的車往回路開去。在轉身以前,蔡仲庚又對他說:「剛才我在電話裡忘了跟你講。胡玲玉知道你們要來匹茲堡,顯得非常高興,說如果她不是在醫院裡,一定會親自下廚燒飯給你們吃。」不知為什麼,這句話突然在他的心裡激起一種感覺,一種許多年來都沒有出現過的感覺,好像他能夠在蔡仲庚的臉上看到她說話的表情,就是那晚他在迎新會上所看到的表情。
他尾隨蔡仲庚的車子行駛在這條看起來相當沒落的街道。這令人感傷的街景讓他想到自己大三時度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他曾經在中午的時候有意無意騎車經過女生宿舍,看看會不會巧遇胡玲玉,問她是否願意一起去吃中飯。那時候的胡玲玉正處於如日中天的階段。他的朋友告訴他,她從一位加州大學來的訪問教授尋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別人都說他們的關係不止於師生情誼。我不會這麼想,只覺得她不需要這麼早就決定自己一生的方向。」他的朋友說。現在他覺得當時應該勤快一點,直接去宿舍找她,聽她談談自己的近況。這也許不會改變她今天的處境,但起碼讓他們見面時有話可說。
他的車子已經行駛在匹茲堡的大街上,他卻沒有抵達一個目的地所該有的興奮感覺。這就跟那天北海之旅的末尾一樣。當基隆終於出現在點起了燈火的山腳下,他們發現這個城市正下著滂沱大雨。每個人都顧不得同行的伙伴,也顧不得煞車系統是否靈驗,只一味地往下坡滑行而去。現在他感覺自己正在做同樣的事情。他開始感到倦怠了,神志也有些模糊不清,只希望能夠及早走進房子裡,喝一碗熱騰騰的湯,洗一個熱水澡,然後倒在床上睡去。
也許人生只是無休止的忙碌,中間偶而會發生一次脫軌的行程,就像那次的自行車之旅。然而你很容易審視自己的過去,卻無法預知自己的未來,尤其是在這陌生的國度裡。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不管明天他能夠跟胡玲玉說什麼,他們很快又要跋涉同樣的路程返回自己的居住地;而胡玲玉也很快就要出院,重新面對這個世界,這個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
後記:這不是真實的故事,但反映了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去國外力爭上游所面對的處境。我一開始寫的時候並不太確定自己的動機,直到今天才了然於心。因此我做了一些修改,將它重新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