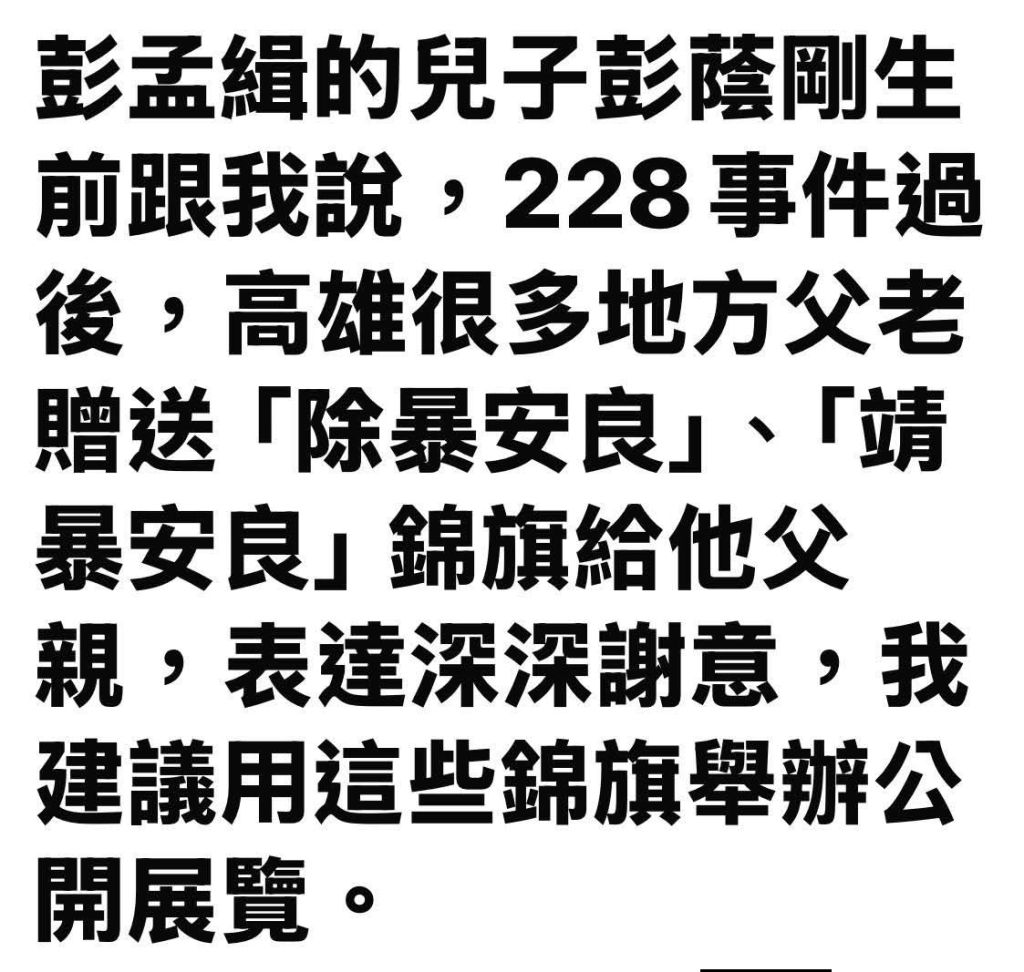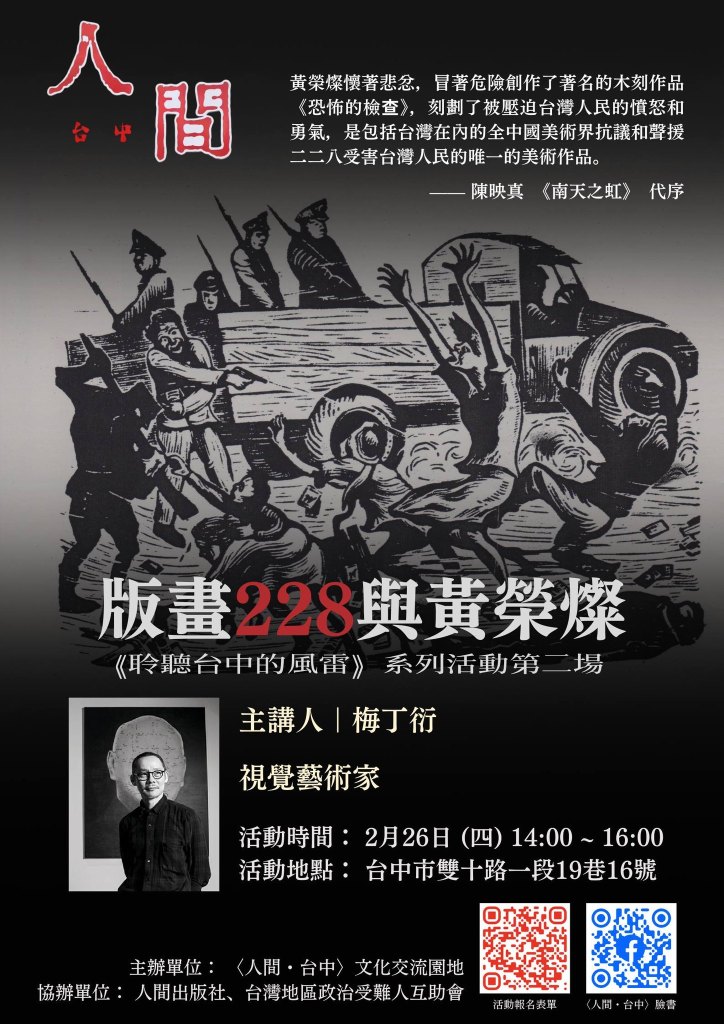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個人對於認識二二八事件有相當強烈的疏離感,疏離感的原因有二:
其一,我的祖輩全都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由大陸來臺,我的家族並沒有任何人直接參與到此一事件中,這個事實對我們產生心理的距離;
其二,從李登輝擔任總統到賴清德擔任總統,總有人要將二二八事件導向「外省人原罪說」,意即這是來自「外省人迫害本省人造成的悲劇」。
這兩者相加到我們身上,對我個人而言,始終有著「莫名所以」的感受,這根本是我們家族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卻打從我一出生到現在,只因我是外省族群(其實對某些人而言,這就是指稱「我不是臺灣人」,該「臺灣人」的定義甚至直接等於閩南族群),就要背負著「犯罪的十字架」,在各種公共場合承受著莫名的指責,好像我們這群人生活在臺灣充滿著罪惡性,這種無端被人標籤化與妖魔化,甚至拒絕承認生活在臺灣合法性帶來的痛苦,現在陸配與其家人大概頗能感同身受,這卻是我青年時間相當沉重的負擔。
直到這兩年來,我開始注意到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尤其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廖繼斌前館長在民國一百一十年(2021)四月八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追思座談中,慷慨激昂替尚未獲賠的外省籍受難者發聲,呼籲政府承認其適用國家賠償的法律地位,並「重新審閱遭駁回的五百一十二件賠償申請案」,尤其再經閱讀唐賢龍在《臺灣事變內幕記》中,記載一則警察單位公布的彙整統計,其中包含外省人死亡四百三十二人,失蹤八十五人,兩者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不禁讓我大惑不解:根據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指出,二二八事件長期是政治禁忌,受難者家屬在恐懼中很難公開訴說其中內容,很多家庭記憶常使用「我們被外省人欺負」這種較口語且較安全的說法流傳,然而,如果這種說法屬實,意即如果二二八事件真是「外省人=加害者,本省人=受害者)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理則,前面這群估計超過五百人的外省人到底是怎麼死亡(或失蹤)呢?
根據蔡正元所寫〈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科學討論〉一文指出,其把二二八事件描寫成「本省籍民眾暴動」與「外省籍軍隊鎮壓」的結構,然而,現在的討論常聚焦在後半段,卻對於前半段隻字不談,然而,正因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這十天內,有前面數字的外省人在社會動亂中面臨群眾暴動(包括毆打、羈押與凌虐)而死亡或失蹤,接著纔會有後面軍隊鎮壓情事的發生。蔡正元指出,這些人涵蓋軍公教人員,甚至有無關於任何機關的一般外省人。外省族群死亡與失蹤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種數字比較像是警察系統將蒐集到的資訊快速彙整後對外公佈的統計,其具體名單尚需要再經比對,避免同一人被重複計算(例如不同單位都回報同一案件),然而,這個數字的存在本身依然具有史料意義,其表示在當時人眼中,外省人的受害現象已經嚴重到需要被警察單位統計與公布,意即外省人面臨死亡威脅並不是後來被人硬加進二二八事件敘事裡,這件事情在當時就已經被視作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僅因「數字可能不精準」否認其所指向的「外省族群受害規模」,這就會把「方法的謹慎」轉化成「敘事的排除」,進而使得外省人受難的歷史事實無法被公共化。更重要的是,外省人在這段期間的遇害並不需要完全依賴前面這一組彙整數字纔能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早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公布其所做《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裡面就直接記載民國三十六年(1947)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臺北多處出現民眾遷怒外省人「濫施報復」,導致外省人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屈辱毆打」的現象,這導致無辜的公務員與其眷屬,甚至來臺短期旅行或經商的外省人都變成「替罪羔羊」,其根據當時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對此事的回憶,當天「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該報告提供的內容來自私人的回憶,其數字未經核實(或許有被低估的可能性),但能讓我們獲得無法被否認的結論: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的確發生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致死的現象。
這種嚴重傷害外省人的現象,從二月二十八日當天爆發後,隔天(三月一日)就開始在全島蔓延開來。譬如張炎憲、胡慧玲與高淑媛採訪記錄的《悲情車站二二八》,就有當時在八堵車站擔任調車員的謝國全親身見證說法,他表示「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並說「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這就出現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提到其發現隱藏在人跡罕至古道中的〈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並表示該紀念碑「恐怕才是真正的全國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紀念碑」,該紀念碑的出現,來自三月一日基隆要塞直屬臺士兵汪烏家在八堵車站被民眾群毆致死(同時還有七名士兵受到傷害),槍枝甚至被奪,這些軍人有帶槍,卻沒有開槍,基隆要塞司令部發文要求八堵車站提供毆打軍人的名單未獲處理,根據《基隆區署二二八事變經過報告書》在當年四月的記載,甚至有流氓數十人持著木棍與短槍直接衝入基隆區署毆打外省籍職員,搶劫其宿舍,奪取派出所的槍枝與彈藥,因此情況惡化到三月九日臺北與基隆宣佈戒嚴。
二二八事件中,三月九日是個關鍵時間點,這一時間點前,就是外省人大規模受到無辜傷害的時間段落,這一時間點後則是國家機制主導的鎮壓。根據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的研究(2025),臺灣省專賣局台中分局科員劉青山就是其中被暴民群毆死亡甚慘的例證。劉青山年僅二十八歲,在三月二日被暴民猛擊昏厥送到醫院,隔天(三月三日)晚上,再有流氓十餘人,衝到醫院中割除正在病床上的劉青山耳朵與鼻子,挖其雙眼,再加猛擊令其斃命。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一一0年(2021)五月一日發布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該報告刊登蘇瑤崇的文章〈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傷亡〉,其未經仔細調查就直接表示根據〈臺中市二二八事變傷亡調查表〉中「劉青山」的傷亡原因寫「打撲外傷腦出血」,備考欄位則寫「三月七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死」,判斷該報告「詳盡較為可信」,蜀蓉居士寫的〈臺中歷險記〉紀錄劉青山還被暴民在醫院殘殺的細節則「顯然是刻意抹黑之說」。
蜀蓉居士所寫〈臺中歷險記〉收錄在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的《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這本書中,該書的出版來自警備總部柯遠芬參謀長擔任社長主持的正義出版社,只要對當年政府不具信任感的人,大可藉由「作者匿名」來質疑其說法的可信度。然而,有關劉青山死因,張若彤指出:蘇瑤崇所稱劉青山死於「打撲外傷腦出血」,其紀錄來自於「三二報告」(該報告由國防部保密局臺中組通訊員江海濤整理),就算蘇瑤崇不願意信任警備總部的說法,寧可相信保密局的紀錄(不知兩者的有效性高低從何而來),然而劉青山在醫院被殘殺的事情,〈臺中歷險記〉並不是唯一的資料,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其工作的專賣局同事在二二八事件後出版《專賣局業務特刊(二二八事件特刊)》,就已經指出劉青山「後送醫院治療,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張若彤質疑拿政府預算來運作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為什麼有「雙重標準」,對來自安徽的劉青山死因如此錙銖必較,卻對於本省籍民眾的死亡,即使不知其姓名,卻表示「姓名不詳但確有死人」呢?
因此,值得反思的現象是:我們當真想要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嗎?王曉波教授曾在《二二八真相》二00二年版的序言中沉痛指出:「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這就是為何廖繼斌館長會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的序中接著指出:「經過了二十三年頭,二二八事件被渲染成『中國人有計畫地屠殺臺灣人』圖像,除了省籍衝突的暗流外,二二八事件還深深堆疊出了海峽兩岸人民的敵意螺旋。」廖繼斌與張若彤並在合著的《我聞二二八:廖進平之死與臺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中的研究指出(2026),隨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補償業務在民國九十三年(2014)末逐漸接近尾聲,體制內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開始出現明顯的性質轉變,其開始往支持民進黨的政黨競選活動靠攏,而與本來「體制內平反二二八」的界線呈現高度模糊的狀態。
這就能解釋我作為歷史學者,縱然從研究方法而言,很容易就能檢視任何人的研究是否符合嚴謹的查證程序,但個人卻始終不想觸碰二二八事件的議題,因為這個議題已經被單一政黨壟斷敘事正義,變成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稍微有不同角度來探討就會被人惡鬥,而無法就事論事的釐清真相。然而,當我在今年(2026)二月八日參加奉元書院潘朝陽院長與統一聯盟王永主席聯合舉辦「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並受邀擔任武之璋主席、廖繼斌館長與張若彤先生演講塲次的主持人,聆聽三位專家的高見,對此深獲精神的療癒與撫慰。武之璋主席指出:當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前,其實是外省族群被大規模傷害甚至殺害的一段日子,這個問題長年不被政府重視,釐清其具體的人數與名單,反而持續掩蓋真相的揭露來展開政治操作,他對此深感不能苟同,大家亟需正視這個問題。廖繼斌館長則指出: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的事實不能獲得補償,更不能被社會大眾看見,讓他這位真正屬於閩南族群的二二八受難家屬同樣蒙受巨大的痛苦,畢竟族群和解需要來自對真相的還原。
尤其是當我看見張若彤先生持續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中道角度,不偏於左右,不偏向於中共與台獨這兩端,撰寫多本二二八相關著作,持平還原那段複雜的歷史,不希望那一輩的軍公教人員蒙受不白奇冤,這讓我對這一議題的澄清,終於點燃起希望的火焰。這讓我不禁回想一段塵封太久的往事:在我童年時期,常見乾爺爺王壽椿先生來家中作客,當二二八事件開始見諸報端,在輿論中發酵與討論,祖籍浙江省溫州市的王爺爺曾經跟我說,民國三十六年期間,他正受電信局的委派,在全臺督導架設電線與電竿,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爆發動亂,閩南人只要看見不會說閩南語的外省人就會狂打與殺害,有位本省籍的醫師收留他在家中躲藏十天,期間還要承受高壓面對暴民的敲門盤問,直到整編第二十一師從上海開拔到基隆,臺北重新恢復秩序,他纔能繼續出門工作,他心中很感念這位充滿正義感的本省籍醫師。王爺爺的這段回憶,在我童年時期閱聽到的輿論經驗中充滿著「政治不正確」,我始終只能放在心上,直到若彤的大作問世,我纔終於能把這段往事公諸於世。
單就二月二十八日當天來說,其實是「外省族群受難日」,大量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在十天內無辜遭到傷害甚至殺害,這件事情豈能說跟我們無關?如果我們保持冷漠,正就是在給有心人顛倒敘事的機會。如果探討二二八事件常要拿現在的人權標準來論斷當年的社會現象,我反覆縈繞心中徘徊不去兩個問題:
其一,面對嚴重剝奪被害者人權的現象,當年的政府除宣佈戒嚴與軍事鎮壓外,還有沒有更恰當的辦法來依法制止暴亂?
其二,現在的我們是否能接受同屬中華民國的同胞被無差別攻擊而覺得無關痛癢?
外省族群對臺灣社會的付出至深且鉅,卻始終被污名化對待,甚至子孫常害怕承認自己的祖先來自大陸,使得有相當大量的年輕人已逐漸淡忘自己祖先艱辛渡臺的犧牲與奉獻,這何嘗不來自於對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過程中引發的恐懼心理?當時我在研討會中呼籲廖繼斌館長與武之璋主席兩位前輩攜手合作,有朝一日各自代表自己的族群,共同設立「二二八事件外省族群受難紀念碑」,讓臺灣族群和解跨出重要的里程碑。畢竟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