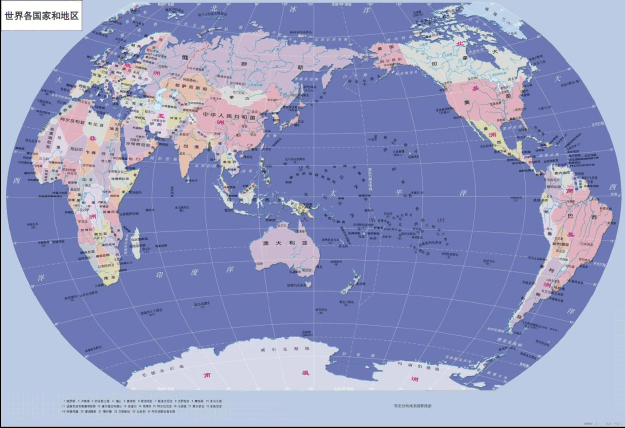曾老師在觀看了電影《可憐的東西》後,寫下了2400字的感想。(參見《電影《可憐的東西》的宗教改革聯想》)文章不長,但卻極富玄思,很能引起人的翩翩連想。我雖然還沒看過這部電影,但竊以為,其實可以脫離電影,而直接以曾老師觀影後的發揮為主要文本,來做一些饒有興味甚且頗富意義的討論。
一、為什麼會有上帝?
上帝造人,其實是因為人認為該有個「上帝造人」,於是有了上帝。用哲學語言來說,上帝不是我們經驗的對象,它是個理性上的概念。理性上的概念是什麼呢?難道還有非理性上的概念?是的,可以這麼說,凡根據感觀經驗抽象而有的,稱為概念。凡根據概念作理性思維(邏輯)而必須要有的,就出現了「理性上的概念」(簡稱「理念」)。
於是,這下就有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請問,這「理念」(被推導出來而被理性認為必須存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叫「真的有」?「凡有所相,皆是虛妄」,就連「眼見為實」的常人所謂的真的存在,在理性的分析下都很可能是虛妄的,那根據經驗再抽象為概念再推導為理念的存在,會是真的嗎?若說感官經驗是假是虛,反而理念是真是實,這說的通嗎?
這真的很有趣。所有問題的討論,在打破砂鍋之後,都會懷疑到提出問題的語言本身(概念)。到底問題在語言所指的對象,還是在語言本身?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道可道,非常道;佛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概念到底是不是真的?所謂「真的」是由概念本身構成還是概念所指的對象構成?…這種真實與概念的糾纏,貫串了整部哲學史。
所以,言歸正傳,上帝只是個「應運而生」的概念,還是真實的?別說上帝了,就連「我」是不是真的都很難說。凡有所相,皆是虛妄,扣除了眼耳鼻舌身意,沒有了色聲香味觸法,「我」還在不在?那「末那」識還能起作用來形成自我意識嗎?感謝佛陀,我們還有個「阿賴耶」,若能轉識成智,海底湧紅輪,破除一切理障,便能直達心源。這也算是為我們認識上帝別開了一個生面。
以上是把「古今多少『學』,盡付笑談中」。認真的學者莫怪。總之,沒有這些「虛妄」的概念,我們實不能以思維的方式定位自我,甚至不能肯定「自我」之存在。(有不云乎,我思故我在。今不假概念,無思,則我還在不在?)但有了這些「虛妄」的概念,「我」又與這些概念同歸於虛妄。真是千古難解。
當然,說難解,嚴格說,也只是思辨理智上的難解。這難解,東聖西聖,心同理同,為我們指出了一個可解的方向,就是由「實踐」而來的直覺。「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古今中外之聖教無不重視修行,此乃破虛還實之唯一解方。不過自文藝復興以來,思維理性大興,於是人類多理障,雖然「思入風雲變態中」,思維可以逼近到上帝跟前,但總差一步之遙;如影歷歷,逼取便逝,奈何?則唯有以理破理,以智破智,看看能否窮智見德,重歸實踐。
二、何以說,上帝只給了人自由(主體性),卻未能給人創造意義價值的權力(道德性)?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為了自身的需要創造了上帝(這一概念)。(這句話如果改為「人為了自己的需要而發現了上帝」,我想宗教徒也可接受了。而這兩句其實意思一樣。)那麼,請問這「需要」到底是什麼?簡言之,就是人與上帝合一的需要。
人看見(發現)了上帝,就代表人需要上帝,也就代表人與上帝是分離的,破裂的,而非合一的。(如果是合一的,反而看不到了,不過是如涅槃之境,根本不必有上帝這個概念。)這令人不能忍受。為何不能忍受?因為上帝就是完美,就是全能至善,人與上帝分離,就代表人知道自己不是完美,不是至善;也就是說,人知道自己壞、有殘缺,故不能忍受。如果人不知道,那人也不需要上帝,如同其他萬物,「奔流到海不復回」,也就罷了。但人偏偏看到上帝,於是一步一回頭,上帝啊,你為何讓我看得到卻摸不到?可望而不可及,那我的救贖在那裡?(苦海無邊,何處是岸?)
上帝給人自由,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轉轉頭,看見上帝,而不至於頭也不能回地「奔流到海」。但上帝不給人道德,因為怕人「自以為是」,(道德不就是判斷是非嗎?)雖然轉頭了,卻不走向上帝,而占山為王,自立門戶,妄自尊大,然後互相攻伐。這不行,這是「道術為天下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個都自以為是,從此不服從上帝指令,永無寧日,上帝受不了,要頒布十誡。說實話,不是上帝受不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相生相尅,上帝早就習以為常。)是人受不了。人受不了,因為這樣的上帝是破裂的,是放任「人神關係」相悖而不統一的;這樣的上帝有也等於無,所以上帝(還記得上帝怎麼來的?)也就必須是「受不了」的。
所以,人雖能自由地轉轉頭,但必須回看上帝,仰望上帝,走向上帝,再與上帝合好如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因此,什麼才是對的?只有順從上帝才是對的。其他廢話都別說了,「方向」的決定權,在上帝手上,免得你們狼奔豕突,四處亂竄,白白浪費了自由。只有上帝才能告訴你方向,才能決定你做的對還是不對。
問題是,上帝他老人家不說話啊!(天何言哉?)說話的都是上帝的人間代理人(先知、聖子、聖王、聖賢、聖徒)。代聖立言,決定你的是非對錯,這就叫「權力」。
本來是聖者為王,聖者才有權力指點江山,作之君作之師,好讓人們認得上帝。後來呢?誰是上帝揀選的人?上帝不說,人的肉眼凡胎也看不出來。乾脆王者為聖,有了權力便是聖者。於是,有權力的人可以替天行道,(誰知道他有沒有假公濟私?)所以他更自由了,別人在他的權力下只可以走向一個方向,他卻可以自由走向無數的方向。這麼大的自由,何必一定走向上帝?也可以走向魔鬼啊,不是嗎?權力使人腐化,上帝的担心,還是應驗了。
曾老師在文中說︰「因為亞當或所有男人都背負著不可違規的正義壓力,想用鉅細靡遺的規範與權力掌控一切,以維持合理的秩序,也是某種程度上的模仿上帝;卻不知這依賴掌控以維持秩序的最大漏洞就在掌控者自己,就在他因被掌控而受壓抑的自由人性正好借此暗渡陳倉,偷偷釋放。原來要有權力才能有自由,卻不知這樣以宣洩壓抑為主的自由只是失控的假自由而不是以創造為主的真自由,於是權力使人腐敗,人性也就向下沈淪為惡魔了!」而本文的上一段,就是在註解這段話。只不過曾老師宅心仁厚,說的更為曲折而周延。意思就是,就算這些掌有權力者本意是好的,是有心維護上帝的仁愛,但無奈「燈下黑」啊!畢竟人不是上帝,替天行道、代聖立言,負担過重,人勉力要以理性之光照亮世界,無奈光亮微弱;勉力去激發更多的光亮,則反而掏空自己,成了照不見的「燈下黑」,「權力」本身成為缺乏光亮的密窟。
「○○○,像太陽,照到那裡那裡亮。」是啊,可惜只是「像」太陽,而非「就是」太陽,所以照來照去,就是照不到自己。

三、新的宗教改革
那麼,怎麼辦?上帝要收回給人的自由嗎?別以為不可能,那就是讓人類都死絕了。你看豬狗牛羊,那一樣不是上帝的受造物?只不過沒有自由罷了。死絕了人類,其他的受造物還在,那就等於是上帝從受造物身上收回了自由。
當然,還有另一條路,就是上帝不但不收回自由,反而還要給人道德(意義價值)的自主權。上帝不再規定什麼是意義與價值,而讓人自己去創造。創造,無中生有,當然是自由的;但上帝不是担心人會亂來嗎?(所以才要宣告真理,要人服從。)沒關係,經過之前的教訓,上帝也學會了,人類自由創造的結果,是助成了自由呢?還是否定了自由?前者就叫善,是真自由,是人人能夠彼此互通,出入無礙,邊界渙漫,水乳交融,浩浩湯湯,橫無際涯,與天地同流,與上帝合一。這種創造,就統稱為「愛」。相反的,如果選擇了否定自由的創造,則結果是縮限了自我,固化了群己的邊界,僵化了人我的定位,十步一營、五步一壘,處處設防,彼此攻伐,…則創造越多,條條框框越多,人越覺得拘束不自由。這樣的創造,固然也是一種自由創造,但卻走向了自由的反面,結果只能是惡。但這也是人自己的選擇,最終是自己懲罰了自己,那也就不勞上帝費心了。而這兩種「自由創造」的路向,也就印證了曾老師在文中所說的︰「道德性就本質地蘊涵在主體性之中」。因為真正的自由,即能夠實現「自由」的創造,必定涵著道德(愛)的實現,否則自由就會走到它的反面,而把原來可有的自由也給摧毀掉了。
當然,自由地創造到底要走那一條路?畢竟還是人類的自由。雖說「自由必然涵著道德」,也就只是「涵著」而已;真正落實與否,還看人自己的實踐與選擇。
然則上帝到底要收回自由呢?還是將道德判斷的權柄一併給了人?這又回到了開頭「上帝造人」與「人造上帝」的邏輯。上帝的選擇,其實就是人選擇。(不有言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要選擇毀滅,就等於上帝選擇了收回自由。但事實上,上帝早就悄然將道德(價值判斷)的權力交到每一個人的手上,否則人又怎有能力去認識上帝的全善呢?(這裡就脫離了電影的述事脈絡,我雖未看,但從曾老師的行文之中可窺得一二。曾師隨影片而演義,故在行文之中不能明顯肯定這一點。然本文脫離影片而依曾文發揮,則此處就可以點明。)
於是,這就連接到了曾師所提的「新的宗教改革」。即是要將人之潛存的道德性,由潛德幽光轉為全面自覺,以對自由的內容作實質的價值釐定(而非僅僅是對自由的形式之肯定),以此來看待、包容、引導人之所做所為,以期「自由」內而與自信合一,外而與道德合一,得自由之利,而又能警覺、節制、即時修正自由濫用之敝,而開啟天人不隔的新宗教精神。
四、現實的問題
本來,文章寫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但如果只是如此,則不足以凸顯曾師此文關係之重大,也不足以表明我讀此文之後何以會有激動之情。蓋以上所說,實是指出人類文明又走到了一個新的關口;從普遍貧窮與供給不足,經工業革命與科學、民主(理性的架構表現)等等之貢獻(主要來自西方),來到了普遍富裕乃至供給過剩。於是,由理性之架構所撐起的廣大空間,使西方從傳統宗教精神的約束中走出,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那麼,這個「自由」要用來幹什麼?曾師此文實際上就是回答了這個問題。所謂「新的宗教改革」,就是指出這個自由理應成為彰顯自由價值的創造,即中國傳統之人文化成(或曰禮樂文明)。
從某個角度說,此論即同於上個世紀早有人提出過的看法︰東方文明將可救西方文明之敝,或所謂「二十一世紀為中國人的世紀」。意即︰在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學理性與社會制度後,取得了與西方平起平坐的權力;然後東方之宗教精神與道德精神,就可以引起西方人的另眼看待,而發現其中實有足以啟迪西方、促進西方宗教改革,以救西方文明之敝。此即中國文明對全世界的貢獻。
然此說當時即信者寥寥,如今更是無人彈此調了。不但西方人不作此想,(較之當年有西皮嚮往東方禪學,存在主義者目光看往東方…等,今日西方學界對東方文化之態度,反而日趨僵化保守,整體呈倒退的狀態。)中國人(不論海峽哪一岸)亦鮮少有此自信。今之中國人欲有所貢獻於世界者,或僅停留在器用技術層次與西方爭勝,而早已丟失自家之道德信念(宗教精神);多數人(含學者)對孔孟老莊等傳統精髓的了解都非常粗淺籠統,甚且因此而輕視之,可謂懷其寶而迷其邦,並不自知何者為自家傳統的獨特與優勝之處,遑論有自信去助成西方文明之更新。
正是因為東西方宗教精神(道德精神)的衰微,造成今日之技術雖然高度發達,早就可以達到全球一體化的運作,但精神卻顯得固步自封,道德理性倒退,陷入高度蒙昧與自私。舉世就在此恍恍忽忽迷迷茫茫的狀態下,讓高超先進的技術把全人類的命運推向一個不可測的深淵。
中美走向對抗,舉世都看在眼裡,而有心人深以為憂。雖然對抗表現在技術的傾軋與經濟的爭雄,但實質上則是西方對「異文明」的極度不信任。(2019年5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有一段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講話,可為代表。)而中國高舉民族復興的大旗,意在走出百年來的屈辱;但走出屈辱之後,下一步的發展方向何在?能為世界帶來怎樣的新精神?則並沒有很清楚的自覺。此所以領導層要不斷呼喚「文化自信」、「制度創新」,但文化自信不能只靠唐詩漢服,制度創新更不能憑空發想;沒有文化精神的透徹反本並與現代性的深入結合,怎麼能迸發出由本貫末的時代新聲?於是中國時下之處境,實不免於「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的尷尬狀態。(此語絕非文章修詞,而是切中當下中國之問題。唯內容申論過於龐大,此處姑以此言聊備一格。還請讀者勿忽略之。)以致於中國雖有雄心壯志,方向大體正確,(如倡言世界共同體、主張共同富裕,強調不稱霸,無意取代美國等等。)然論述未臻完備,目標有欠鮮明,導致桴鼓未能相應,上下多有猜疑。
七年之病,尚需三年之艾;況世局沉疴由來已久。然今不蓄艾,則永無了期。如果我們不願見到「上帝收回人之自由」的悲慘結局,則必然要以「但問耕耘」之精神,勇於蓄艾。而蓄艾之道,在西方,為找回並革新其宗教精神;在中國,則為中國文化精神之反本與開新。前者留待西方有識者為之,後者則在於我們內聖修身精神之恢復與不必依附政治之新外王的創造。所謂「新外王」,即秉反省之誠與仁心之明覺,開展出基於真誠與愛的人際關係(不止是互利共贏),開發基於兩性平等與道德之愛的新夫妻關係(不止是兩情相悅與彼此愛慕),讓家庭真正成為情感(包容)與愛(推擴)的基地;而讓所有人都成為擁有創造意義、實現價值的真正自由完整的人(不止屬於掌握權力的人)。而這,也同樣是西方新的宗教改革所應達到的目的,正所謂「殊途而同歸」也。
當然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文化復興與道德創新運動,千絲萬縷千頭萬緒,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更何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若仍只是袖手談心性,隔山觀虎鬥,則是未知時局之嚴峻。知世局危險,但以為上述過於迂闊,只想依靠政經軍事決出勝負,則不知那只會拖延問題,冤冤相報,自陷斷港絕潢,沒有出路。今日問題之總根源,在於人心之狹隘,以自由之心卻自陷於「不自由」之中。此即是人憑藉技術之發達,勇於爭取自由而放棄上帝教導,卻又找不到走回天國之路;「人心」「道心」相背,自由與意義相離。故治本之道,只有如上文所示,凡有所覺者皆當勇於實踐,以帶動更多的真正的道德創造,成就更多「充實而有光輝」的人;最終積少成多,扭轉世局。則或經過數十百年之蓄艾,數百年來之頑疾終將痊癒,而為人類文明再開一新局面也。
我想以上這一番議論,乃順曾師文章之義理脈絡而所當有,應不謬於曾師文章之微言大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