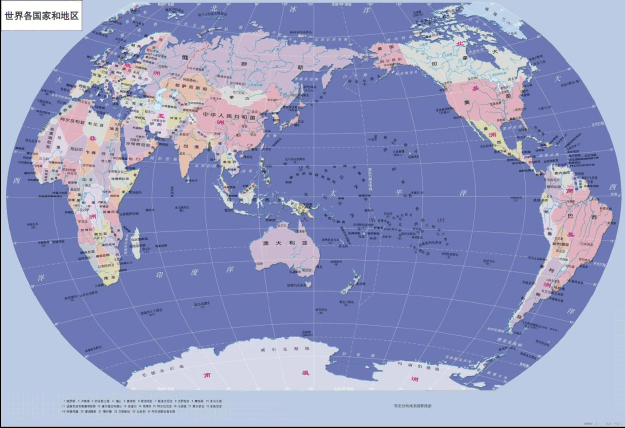如果只從解嚴後大型佛教團體的興盛回望,很容易會誤認臺灣漢傳佛教的欣欣向榮只是一段突如其來的宗教奇蹟。但把時間軸拉長,我們會看見更清晰的輪廓:
從清朝統治開始,臺灣已累積包括齋教在內民間佛教實踐的土壤,然而,日據時期的宗教政策帶來的衝擊,使得佛教的制度與空間都面臨嚴重的異變。就在這種真空狀態首先出現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臺灣光復後,卻因民國三十八年(1949)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來自大陸,有著叢林訓練、佛教教育與改革思潮的僧侶與居士大量來到臺灣匯聚,這些人各自從僧團制度、戒律傳承、弘法教育、慈善組織與海外網絡埋頭苦幹,立刻填補真空,推動漢傳佛教邁往制度化與現代化的發展樣貌。
這段歷史如果只被視作「外省人把佛教帶來,讓佛教在臺灣壯大」,這會遮蔽兩個更關鍵的面向。第一,戰後臺灣的弘法環境並不平坦,戒嚴體制裡,政府對集會管理甚嚴,加上社會對宗教的刻板印象、尤其省籍差異帶來的語言距離感,都使得佛教要走入公共領域,就得付出巨大的奮鬥;第二,更值得強調的現象是,佛教在臺灣的壯大發展,不僅是教團規模的擴張,更在臺灣社會逐漸生出「具有佛教意義的族群和解共生」的場域:大量不同族群的人來到同個道場,在同段時間共修,或者共同擔任志工,彼此視作同門,再把彼此的差異置放在可被理解與尊重的位置,這讓漢傳佛教在臺發展的歷史,變成各族群在佛教團體中和解共生的歷史。
清朝統治臺灣時期,佛教寺院提供誦經、超薦、齋戒與教化等機能,並與善堂、宗族與鄉里相互交織成互助網絡。這種佛教生活化的型態,長時間培養出基本的宗教感受與社會信任,使得人們知道寺院是可供求助、寄託與行善的空間。然而,日據時期把宗教場域推向極其複雜的狀態,尤其日本佛教各宗派進來臺灣,加上殖民統治的嚴厲措施,寺院財產與僧侶資格都受到控管,使得漢傳佛教相對來說變得極其壓抑。正因既有傳統在地化的佛教與殖民統治產生衝撞,留下需要被重新回答的問題:佛教要採取何種傳播型態進入臺灣社會?僧團如何自我整飭其紀律?弘法如何離開寺院來到社會,最終不失其法脈正當性?
戰後佛教重建的第一階段,重點是把骨架搭起來:這包括架構出僧團資格、傳戒秩序、代表組織與對外發聲的合法管道。立基於此,民國元年(1912)成立於北京,民國三十八年在臺灣重整的中國佛教會,提供僧團與社會間一個可被清晰辨識的制度框架。這個框架的形成既與政府治理宗教的需要有關,更與佛教圈自身對僧團整頓、弘法協調與國際聯繫的期待相互關聯。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的制度骨架並不是只由漢傳叢林體系單獨支撐。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圖克圖,籍貫青海省互助縣,蒙古語稱活佛「呼圖克圖」,1891—1957)是格魯派(Gelug)中地位極高的活佛,長期擔任政教溝通的角色,並在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出任中國佛教會首任會長。
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都是中國佛教,章嘉活佛的存在提醒我們即使戰後臺灣社會的主流佛教係漢傳佛教,但宗教版圖裡已出現被制度性安置的藏傳佛教位置。當時藏傳佛教尚未形成大規模的擴散現象,直到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前後,海外藏籍喇嘛來臺弘法的規模纔明顯擴大,藏傳佛教各派學會或組織陸續成立,開始在臺灣形成更清晰的社會能見度。回到漢傳佛教來觀察,僧團制度的建立同樣仰賴多位具外省族群背景的高僧與居士。白聖長老(1904—1989),籍貫湖北省應城市)長期在中國佛教會甚至國際佛教組織中居於要津,其重視僧伽戒律與對外聯繫,他象徵著戰後漢傳佛教在社會轉型中,如何使用組織化型態維繫僧團公共性的路線。

東初長老(1908—1977,籍貫江蘇省泰縣)是太虛大師(1890—1947,籍貫浙江桐鄉市)弟子,因此係嗣法臨濟並兼承曹洞的著名禪師,其著重於「文化弘法」,重視刊行佛經與出版期刊,將其做成制度化的措施;南亭長老(1900—1982,籍貫江蘇省泰縣)著重華嚴教學,來臺後創立華嚴蓮社,長期講經說法,讓教理研習在都市空間中構築堅強的聞法社群,長期維繫攝受信眾,這與其「以教入行,以行驗教」的主張與節奏有關。南亭長老曾回憶向應慈老和尚(1873—1965,籍貫安徽省歙縣)學習的過程中,自己日復一日的跟著其師聽講,研讀經論,坐禪與結七不輟,其把華嚴教理落實到生命中,使得華嚴宗變成結合哲學與實踐的生活法門。
來到淨土傳統,道源長老(1900—1988,籍貫河南商水)一生強調持戒念佛,行解並重,並在傳戒與戒壇的運作中具有重要角色,其重建僧團秩序,讓佛教脫離「香火信仰」,使得僧團制度更加清晰。悟明長老(1910—2011,籍貫河南省商水縣)傳承臨濟宗,長期弘揚觀音法門,被稱為「觀音老人」,拿大悲懺來當作修持,使得信眾在共同禮懺中凝聚;這種著重共同儀軌與共同修持建立群體倫理的辦法,對於跨越族群凝聚成共同體甚屬有益。此外,李子寬居士(1882—1973,籍貫湖北省應城市)曾參與中國同盟會,屬於中國國民黨創黨元老,在戰後佛教組織與社會人脈的連結具有重要性,曾經拯救包括星雲法師在內的僧侶脫離牢獄並獲得釋放。
要讓佛教成為獲得臺灣社會普遍接納的公共宗教,還需要媒體、教育與青年的共同支持,這往往靠居士網絡來補齊。周宣德居士(1899—1989,江西省南昌市)是戰後臺灣佛教居士運動的重要人物。他極其敏銳看見:如果佛教依然停留在神佛不分的民間想像中,就無法進入知識青年與中產階層的生命世界中;因此,周宣德居士利用廣播節目來「空中弘法」,提供獎學金給學生,推動佛教文化傳播,並鼓勵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讓佛法在校園中被閱讀、討論與研究。慧炬體系所形成的公共平臺,使得佛教的跨族群傳播出現新路徑:即使家鄉口音與地方人脈存在著門檻,文字與思想依然成為共同語言,讓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套概念框架裡對話。
從佛教社會史的角度看,凝聚青年的意義不僅是「吸收新信眾」,更在於其改變佛教共同體的組成型態。傳統社會的信仰共同體往往依附於聚落與宗族的關係,在校園組織社團,辦理讀書會,使得「共學共習」替換「同鄉同族」,讓人們採取同學與同修的角色互相辨認並凝聚彼此。這種著重知識與修持做核心的共同體,更容易天然跨越族群界線,把佛教帶往專業的公共討論環境中。戰後臺灣佛教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莫過於大型教團的全球化發展。這些教團並不是各自靠其大師的奇魅,而是把宗派法脈、思想主張與組織技術結合,架構出教育系統來培養人才,採取共同參與的行動辦法來凝聚信眾,尤其懂得使用跨文化的語言來向外傳播。
這些漢傳佛教大師的出身背景常是來自外省族群,這些人無不經歷戰火流離的時空形成高度的公共使命感,常帶著強大的願望來臺弘法,並把大陸叢林的僧團訓練帶進來實施。創立佛光山的星雲大師(1927—2023,籍貫江蘇省揚州市)屬臨濟宗的重要傳承者,長期倡導「人間佛教」,著重文化、教育、慈善與共修作為弘法支柱。在人間佛教的語境裡,佛法不僅攸關個人解脫,更要回應社會的倫理需要。因此,道場不只是宗教空間,更是教育、藝文與公益的平臺。星雲大師這種主張有著極具跨族群效果的特徵:其把人們的身份入口從族群轉向共同行善與學習,更在共同實作中凝聚共同的宗教認同(佛光人),族群差異在其中被安放而不會被放大。
創立法鼓山的聖嚴法師(1930—2009,籍貫江蘇省南通市)兼承曹洞與臨濟兩脈的禪宗法脈,並提出「人間淨土」與「心靈環保」的理念。他在生平回憶中,數度談到自己童年時期即出家,因戰亂而還俗,在民國三十八年因從軍而跟著政府來臺,服役十年後再度披剃出家的經歷,最後在東初長老門內重回僧伽生活。這段「離開—回歸」的生命路徑,使得他對於人心的焦慮與制度的設立都有強烈感受。聖嚴法師是第一位親自就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高僧,其思想主張是把禪修整理成可提供人理解與鍛鍊的知識,尤其變成可在當前生活中落實的工夫,並把佛教倫理解釋成能回應焦慮與衝突的公共語言。
創辦慈濟宗的證嚴法師(1937—,籍貫臺中市)被視做臺灣漢傳佛教公共化與全球化的重要領袖,她的族群背景是閩南人,然而,其能形成大規模的志工團體,與其師父印順導師(1906—2005,浙江省海寧市)的思想脈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印順導師強調教理清明,重視佛法在人間的實踐,其詮釋常被視做人間佛教思潮的重要一支。證嚴法師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在印順導師門下出家,並於民國五十五年(1966)創立慈濟前身(慈濟功德會),把大乘佛教的菩薩道做制度化的轉化,變成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四大志業。慈濟的語言既有佛教的慈悲,更帶有儒家重視禮敬與修身的特質,因而更容易在家庭與社區的生活中實踐。
惟覺老和尚(1928—2016,四川省營山縣)創建中臺禪寺,其法脈源自五宗法脈虛雲法師(1840—1959,福建省晉江縣),強調通過禪修展開對僧團訓練與戒律生活的重整。中台路線高度重視紀律化的共住與共修來建立共同體,其群體著重於「共同作息,共同用功,共同持守」來維繫。在這樣的修行場域裡,族群差異並未徹底消失,但其社會效益被重新排序,更重要的辨識角色不再是「你從哪裡來」,而會是你願不願意「共同修行」。惟覺老和尚高度重視僧眾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這三大領域,將佛法落實於各階層中,並提出學術化、教育化、藝術化、科學化與生活化這「佛法五化」來做弘揚佛法的方向,呈現出佛法接引眾生的豐富層面。
除這四大教團外,自民國七十年代末至民國八十年代而降,臺灣漢傳佛教呈現多中心擴張,這不只意味著更多元的道場成立,其弘法語言更為多樣性:有的偏重教理次第與長期聞思,有的強調宗教對話與和平倫理,共同點則是都在臺灣社會中覓得可持續發展的組織型態。日常老和尚(1929—2004),籍貫上海市)創辦福智團體,拿《菩提道次第廣論》作為核心教材,建立長程聞思修的次第修學體系。其幼年由父親教導背誦四書五經,後來在佛法中覓得更完整的慈悲與智慧,這樣的生命經驗,使得福智在弘法語言上把儒家的倫理與佛教的菩薩道連接起來。福智的修學架構大量使用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次第觀,使得其變成一整套人生規劃的教育工程。
創立靈鷲山的心道法師(1948—,祖籍雲南,生於緬甸臘戌省)曾說自己是「出生在緬甸的雲南人」,流浪於滇緬山區,曾參加游擊隊,民國五十年(1961),時年十三歲的他隨著滇緬孤軍撤退來臺灣,後來出家於佛光山星雲法師門下,其傳承漢傳佛教臨濟宗法脈,結合緬甸南傳佛教上座部瑪哈喜禪法與藏傳佛教寧瑪龍欽寧替大寶伏藏法脈,更拿觀音菩薩大悲十心做日課來接引眾生。心道法師主張常把禪修落實為「平安」與「寧靜」的生活工夫,並創立世界宗教博物館,展開跨宗教對話,將佛教語言推向更普遍的和平倫理。靈鷲山的例子向我們顯示:臺灣佛教的全球化發展,重點在使用跨文化的語言,把佛法當作化解衝突與促進共生的公共資源。
我們更不禁從中觀察到:漢傳佛教在臺灣的全球化發展,隱然已有將南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都融為一爐的特徵。尤其每個教團創立者,都有意識把人的身世背景淡化,使得參與者的生命從「血緣與籍貫」轉向「緣起與共修」。在共修並擔任志工的過程中,信眾首先在面對彼此的苦與願,攜手禮懺、坐禪、訪視、救災甚至興學。當人把「同修」當成主要的角色認同,省籍就不再是最重要的分類。這並不是把彼此的生命經驗全然隱藏,而是讓彼此共同承擔某項志業,在實踐中累積信任,使得差異獲得理解與尊重。用佛教語言來說,這是種把「身分」轉向「緣分」的修行:承認因緣各異,卻在同體大悲與互依互助中,喚回人與人和解共生的契機。
立基於此,當我們回首檢視戰後這些外省高僧或外省居士的貢獻,就會發現其弘法的堅苦卓絕精神實在令人敬佩不已。這些大師在全然陌生的環境中,竟然能開創出可長期運作的佛教組織型態,藉由叢林訓練與戒律傳統,使得僧團自律有其依據,更拿現代知識來與佛教對話,發展出世人可毫無違和感參與的佛學教育,藉由居士網絡與社會實作,更使得佛教進入到媒體、校園、醫療與慈善的體系中。這些條件疊加起來發展,讓臺灣社會成為漢傳佛教面向全球輸出的重鎮。大師的生命風姿樣貌各異,卻有個共同點:這些高僧無不在人生的成長歷程中,在大陸經歷過戰火洗禮,在亂世中淬鍊出堅忍不拔的人格,最終在承平歲月中開創出佛教的志業。
當然,我們景仰這些佛教大師在臺灣的貢獻,同時要避免兩種過度簡化的思維。其一,把漢傳佛教的成就完全歸因於這些外省高僧或外省居士,彷彿清朝而降在地土壤適合於佛教發展的宗教氣候被輕易抹煞,更不能漠視本省各族群僧眾都在這些過程中善加護持與成全;其二,把這些外省高僧或外省居士視作可被輕易忘懷的過客,彷彿臺灣漢傳佛教的高度發展能在沒有這些大師的經營中,按照同樣的速度與規模自然而然存在。更契合於事實的說法是「兩者相互成就」:在地土壤提供可落腳的佛教傳播環境,具有外省族群背景的佛教大師帶來法脈,加速其制度化與公共化的發展,跨族群的弟子與信眾,則把這些大師的理念變成可持續耕耘的社會實踐。
因此,當我們聽見網路平臺常見某些偏激言論,諸如在去中國化的浪潮裡,時不時就會出現「外省人滾回大陸去」這種排他性甚高的政治語言,其展現的問題不只是粗暴的語言,更在於這種說法把某個族群當成可被全面否定的對象,忽略戰後臺灣社會的飛躍發展來自各族群共同攜手合作的事實。外省高僧或外省居士在臺弘法、辦學、出版、救災與建寺,甚至培育高等教育人才的歷程,早已被嵌進臺灣社會的文化肌理中,被世人公認是漢傳佛教發展史上極其輝煌的一頁篇章,當你否認這個群體的存在價值,包括來自這一族群的大師留下來的精神資產,都跟著被你全盤否認,難道要漢傳佛教全面退出臺灣,纔能還給某些人心中「純淨的臺灣」?
從佛教倫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否定同樣違背緣起互依的常識。從島嶼的佛寺到全球的道場,漢傳佛教在臺灣七十六年來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不是任何族群能獨占的偉業,而是眾緣和合的共同果實。當我們懷著更寬廣的視野,就會發現臺灣能成為漢傳佛教的世界重鎮,正來自我們在面對族群的衝突與差異中,培養出共修與共行的態度,這顯然是族群和解共生的不二路徑。回首漢傳佛教在臺灣的發展,旨在提醒我們:不論政治認同如何分歧,對人的基本尊重始終都是共同生活的底線。當我們認識這些在島嶼上傳法的佛教大師其成長的背景不只來自當年生死流離的大陸,更始終來自儒佛會通的中華文化,這更有益於我們培養弘法利生的博大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