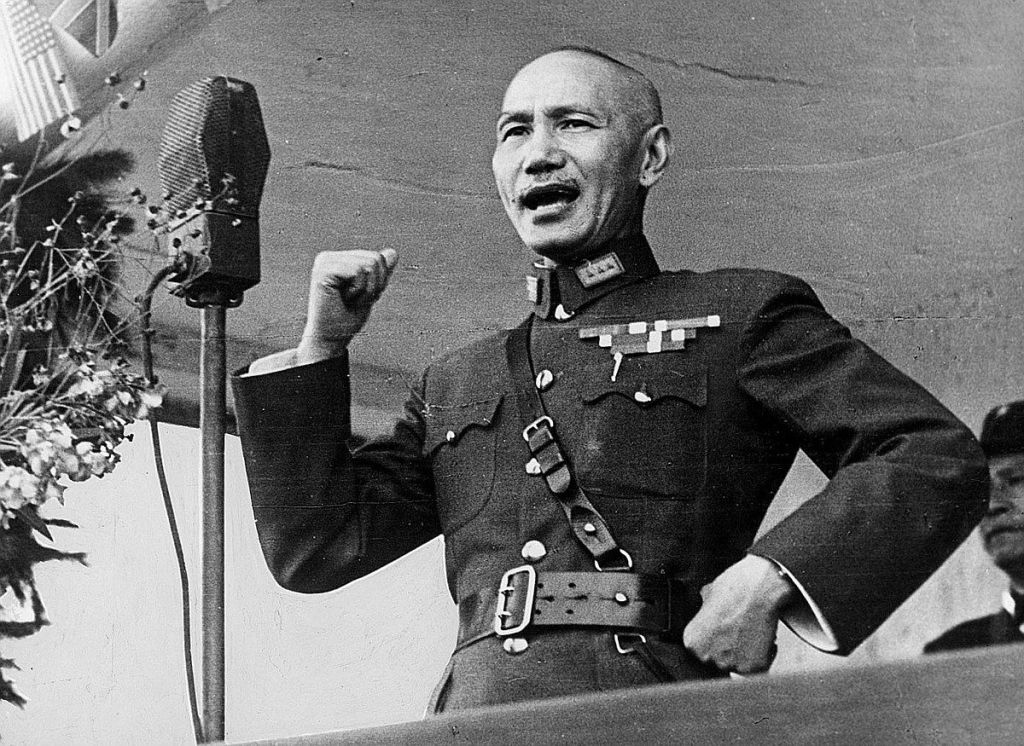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