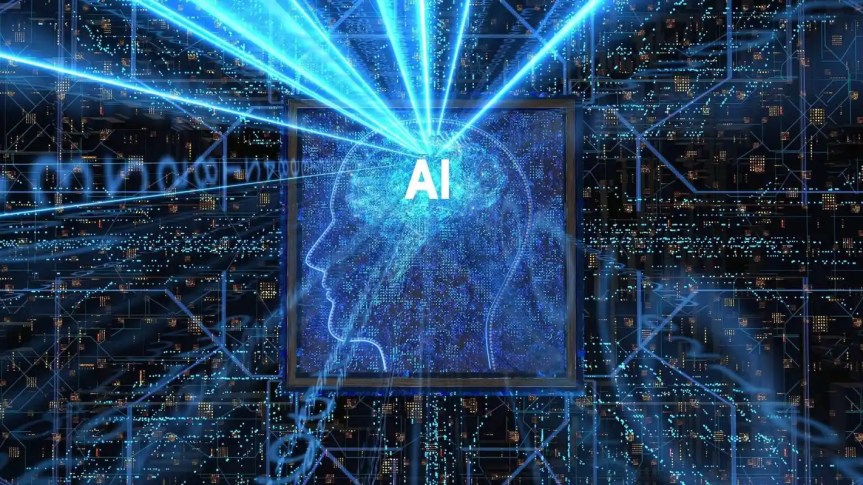夜色降臨拉薩,高原的風冰涼卻澄澈,遠處紅白相間,宮頂金碧輝煌的布達拉宮與山體合而為一,在暮光下靜立,雪山是宮殿,宮殿是雪山。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脫下靛藍的袍子,換上貴族青年的便裝,悄然下山。
離了宮殿,他就是達桑旺波,不是六世達賴喇嘛,不是眾人膜拜的活佛,不是雪域最大的王,就只是個個悸動於凡情,期盼人間愛情的少年郎。
拉薩的街頭,是達桑旺波的場域,廟市熱鬧,歌聲響起,人群歡樂,火光旁起舞的人們,影影綽綽。
那個少女,出身於身手矯健的牧民家庭吧?面貌姣好清秀,卻又帶著不屈的野性,背著木雕弓箭,皮膚被陽光曬得健康,眼睛像湖面被風拂過般明亮。
達桑旺波問:
「你是誰?」
明亮的眼睛笑了,比星光明亮。
「卓瑪。」
少女笑著,伸長著手指向遙遠的南方:
「那邊是我家。」
兩個青年男女一下子就熟稔起來了,在歌聲與夜風中並肩而立,心跳劇烈異常,撲通撲通的兩顆心,漸趨同頻。
自那夜後,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白天在經殿中誦經,輕閉雙眼,搖動簽筒,在濃濃的香霧之中,想著卓瑪的一頻一笑,腦中迴繞著卓瑪的聲音。
夜色最濃時,倉央嘉措總是換上華麗的服裝,避開所有的僧人與護衛,離開經殿,悄悄的下山。
達桑旺波和卓瑪最愛在河邊吃糌粑,躺在草坡上仰望星辰,在客棧中相擁、糾纏,跟著人群擠在市集邊緣談天說笑。
青年男女的心對遠方、對未來、對永遠是憧憬、是期盼、是熱切的;天長地久,地老天荒也就這樣了吧?
不過,達桑旺波老是不談家人,不談自己,惹得卓瑪老是問:
「你到底是誰?你的身分很高貴嗎?為甚麼你眼睛裡老是有著濃濃的憂傷?」
達桑旺波老是沉默,什麼都不能說;但每每在短暫的哀傷之後,隨即又高興了起來:
「不要老是問,你只要知道我是拉薩街頭最美的情郎」。
有一天,布達拉宮舉辦祈願法會,進行大威德金剛跟喜金剛的灌頂與教法傳承,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率領眾僧祈求和平,為眾生祈福;數十萬信眾聚集參與,卓瑪也來到了布達拉宮前。
宮門打開,僧侶列隊而立,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從殿中走出,法像莊嚴,金冠與袈裟在陽光下閃耀。
卓瑪擠在人群中,看著突然變成法王的情郎達桑旺波,腦中一片空白,張口結舌,身體完全無法動彈,周遭雷聲般的讚誦、歡呼,恍若天邊飄來的聲音,微弱又遙遠。
倉央嘉措緩步經過,目不斜視,卓瑪看著眼前的情郎眾星拱月般地被護衛擋住,不可觸及,感覺那麼近,實際卻又那麼遠。
一陣風吹來,很冷,雪在兩人之間飄落。
幾天後,清朝大皇帝認為六世達賴喇嘛的選定不但不符轉世規定,本人也對政治抱持疏離態度,恣意詩歌、縱情飲酒、不守清規戒律,遂出兵入藏,要押解六世達賴入京。
那一夜,夜裡,倉央嘉措再度潛出宮殿下山;好不容易找到卓瑪時,少女也正收拾行李,準備離開拉薩返鄉。
倉央嘉措問:
「你要走?」
卓瑪點頭:
「你是活佛,我是牧民,我們不可能在一起。」
倉央嘉措情緒很是低落:
「我也要離開了,文殊大皇帝震怒,派兵來抓我去北京」。
卓瑪捧起他的臉,像以前一樣的溫柔,有些擔憂:
「沒事的,大皇帝也是活佛」。
倉央嘉措最後一次擁著卓瑪,低聲說:
「我不要做活佛,我要做陪著你走路、喝茶、放牧的情郎。」
卓瑪紅了眼眶:
「下一世轉世,記得告訴我地方,我好去找你」。
兩人緩緩離開,卓瑪轉身走進夜色,背影如風中的燈火,也就一瞬,便再也看不清。
倉央嘉措被康熙皇帝派兵押送北京,行經青海湖邊時坐化,時年23歲。
在千山之巔萬水之源的雪域,在湛藍的天空靄靄的白雲之下,有著皚皚的雪峰跟寬闊的高原。
呼吸着稀薄而純凈的空氣,藏族老阿媽卓瑪做著針線,口中呢喃著些什麼,講述過去的年華與現在的時光吧?時光在她的臉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幸福卻長久地在她靈氣不減的眼睛裡閃着不滅的光,她喃喃的說著:
「他說,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