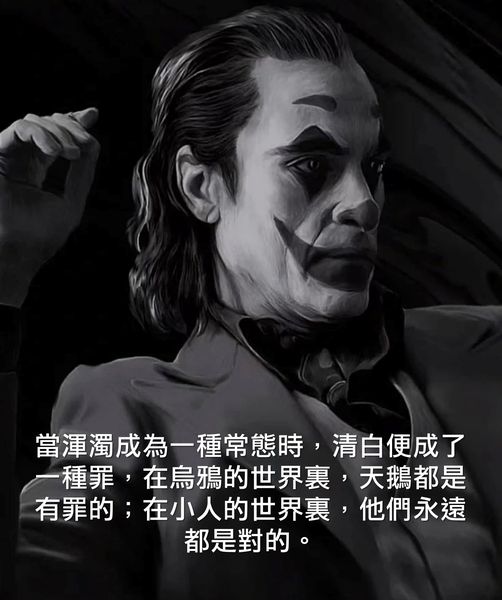我喜歡小孩,中學畢業雖考上成大夜間部,因生活費沒著落休學回家,恰碰到幼弟出世,就歡喜地照護,直到他四個月後病故,此後鄰居小娃或自家小輩,都讓我心生憐愛。
我崇尚大男人主義,曾自稱沒能力養家絕不結婚,所以晚婚38歲才做爸爸,但卻未有養兒防老概念,結婚至今50年,家中一切生活費用都由我支付。看到台灣生育率低減,似乎不再重視養兒育女,見證父母養育我們子女的艱苦,自己這代也的確不敢多生育,無視養兒防老。
之前自己奉養父母沒感猶豫,父母走了也沒感不孝,現在自己老了,只重天倫之樂,不受兒子奉養,也沒遺憾或不快。看到年輕女孩不結婚,抱著同情憐惜,因為女孩長心眼會用腦了,時下許多女孩能力條件超越男孩,沒心儀對象,憑什麼為他洗衣燒飯,照顧小孩再變黃臉婆。何謂心眼?可說是懂得思考懂得比較和了解,從知到識到悟,知道輕重利害,所以有所取捨。傳宗接代無所謂責任,也沒道德束縛,男女配對只存在緣或愛。
看到日本國力衰退,主要原因在年輕人減少了,老人把持政權,只想守護既得利益,抱著殖民地思想見識不深遠,一個老化國家,怎會有生產力、競爭力、成長力?經濟是國家生存唯一命脈,年輕人是經濟建設主要動力,不事生產玩弄金權,沒讓年輕人參與建設和生產,沒使經濟起飛,美國已日漸衰敗。由此,養兒目的在延續國家命脈,避免國家老化!所以國家需要青年,不管國防還是經濟,青年是國家的棟梁,須從幼兒開始培育,更須全盤有計畫地教育。
父母養育子女,子女孝順父母都是愛與天性,但供養父母則得斟酌子女能力,父母不該超生或不知儲蓄,也不該供養成年子女,給自己找罪受。人性純潔,倘天倫敗壞,除父母教養失敗,更在環境缺陷。養兒是人性,我75歲得孫子發自內心喜悅,感覺像中樂透。然而沒有愛與代代接力,國家怎能永續,因此延續國脈養兒防老責任在國家,所需經費,該由超額財產和遺產支付,畢竟過多的財產只造成奢侈浪費與揮霍,反誤了子女身心的健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