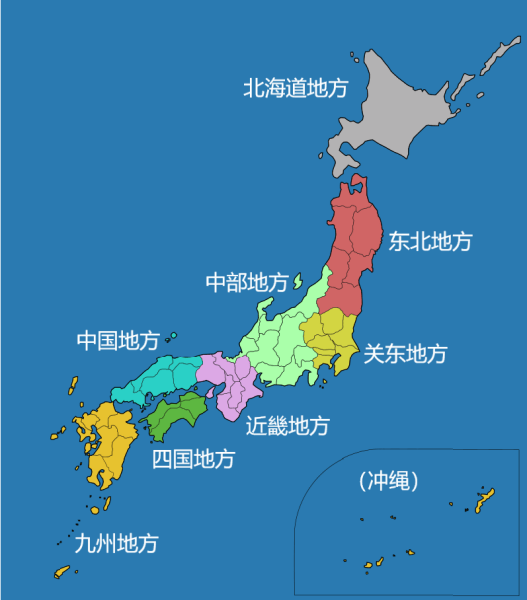看到名作家楊照,在其《楊照書話》中,如此描述日本基督徒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大作;稱該書為──
『滿足西方人對日本的好奇,也準確地凸顯了日本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尤其是西方人從表面看最感困惑又最難理解的部分。』
個人深感驚訝,如果日本的武士道文化,能夠以新渡戶的那本書為典範;那麼日本早年的那本《葉隱聞書》的存在,有何意義?而據個人所知,那本書乃是日本在二戰末期,每家必備的經典。。。
相對言之,新渡戶的那本《武士道》,原書是用英文寫成出版的,是否不過只是日本對西方重要的文宣作品吧。。。我們島嶼曾受日本深度宰制,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在那本《葉隱聞書》中,有這樣的鼓舞──
「一旦在本心中,附以辨別力、分別心,就會成為膽小鬼。在武士道裡,生出辨別力、分別心,能一往直前嗎?」
「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武勇的品德須有狂質』……這種認知與我的覺悟如此不謀而合。打那以後,我決心更要發狂。」
另外,上次讀楊先生大文,其中由早年京都帝大與東京帝大的差別到今天兩大學之不同。
個人所知,日本明治維新後,有所謂「國體論」天皇絕對主義的傳統,戰前,大正民主下,確實學術比較開放,但是仍有「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二戰後,雖在盟軍之下,有其開放與自由,但是其學術研究的框架仍然有其嚴格的侷限;因而,如名學者戴國煇先生在日本研究台灣近現代史,就有其不可碰觸的問題。。。
京都大學怕與東京大學的差別,在對於台灣史研究的範圍內也沒有太大的差距吧。。。
記得幾十年前,拙作出版時,一位長輩慰勉有加,我實在不敢高興,甚至很感悲痛。。。幾乎併淚的,因為,坦白地說,個人自知資具有限,又非歷史專業,那樣明顯的重要問題,居然要等待我這個外行者來提筆。。。過去的學界是如何怠惰,或是已被長期閹割了啊。。。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