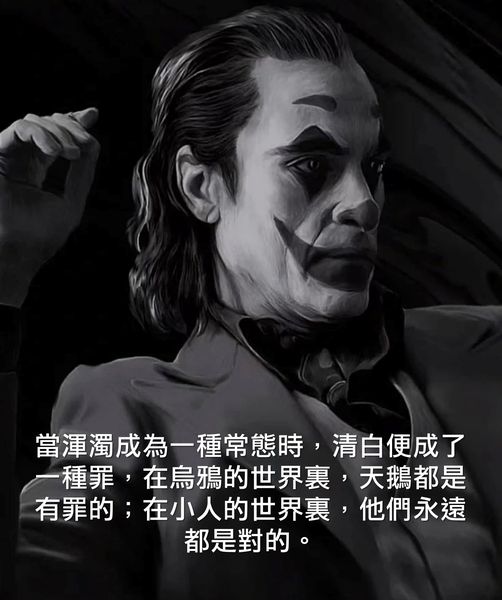當渾濁成為一種常態時,清白便成了一種罪;在烏鴉的世界裏,天鵝都是有罪的;在小人的世界裏,他們永遠都是對的。如同魯迅《狂人日記》之中的「狂人」,又如同《長明燈》之中的「瘋子」。
因為在一群渾濁的人中間,清醒者屬於異類,所以清醒便成了一種錯誤。
魯迅在1925年3月5日創作了短篇小說《長明燈》,最初連載於《民國日報副刊》,後來收錄在小說集《彷徨》之中。
《長明燈》這一篇小說和《狂人日記》相似,是一篇思想啟蒙的諷刺小說,魯迅在其中創作了一個人物「瘋子」,講述了「瘋子」想要吹滅村子廟中的長明燈,引起了全村人的恐慌,最後被全村人關押的故事。
魯迅塑造的「瘋子」形象,代表的就是在渾濁常態下,唯一的覺醒者。
魯迅在1918年寫下《狂人日記》,7年之後寫下了《長明燈》,所謂的「瘋子」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瘋子,而是在一個渾濁狀態下,世人都奉行錯誤觀念時,反而將覺醒當做了錯誤。
他的「瘋」並不是「瘋」在身上,而是「瘋」在了覺醒上,他敢於摧滅由封建思想和固執民眾共同建立的長明燈,而且他也意識到燈滅了,但是渾濁仍然存在。
所以「瘋子」說:「我知道的,熄了也還在。」
他忽又現出陰鷙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斂了,沉實地說道,「然而我只能姑且這麼辦。我先來這麼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他說著,一面就轉過身去竭力地推廟門。
然而,這盞長明燈對村民來說,是傳統的象徵,是吉祥幸福的預兆,如果燈滅了,便會招來災難,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面,這盞燈從未熄滅過,他們怎麼會允許一個「瘋子」將燈熄滅呢?
當人們認同了某一種價值觀和生活環境,就不會察覺這個環境之中存在的問題。
所以就有這樣一句話:「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反之也是一樣,當一個人相信了一個錯誤的價值觀後,不僅不會懷疑這個價值觀的問題,反而會認為正確的東西有問題,所以大家都將這個人視為「瘋子」,他們絕不允許「瘋子」去吹滅自己所信仰的長明燈。
有形的長明燈在廟裡,而無形的長明燈則在心裡,就算能夠把廟裡的燈吹滅,但是也吹不滅心中的長明燈。
而且任何一個時代都有長明燈,任何一個群體也是如此。
在另一個群體中,或許並不是因為封建道德塑造的長明燈,而是因為群體的愚昧和無知,這就是「群體劣根性」。
對於群體來說,他們迷戀的是群體的歸屬感,缺乏的是個體清醒的認知,在歸屬感之中尋找優越感,而且他們更擔心被群體孤立的冷落。
蘇格拉底有一次上課,拿出一個蘋果,問在座的學生:「誰聞到了蘋果的香味?」
這個時候一個同學舉起了手,當蘇格拉底從每個學生面前走過,並叮囑大家,讓大家仔細聞空中的氣味時,又重複了一個剛才的問題,這次,其餘的學生都舉起了手。
最後蘇格拉底說:「這只是一枚假蘋果,並沒有香味。」
當時代在變化,但是群體的劣根性卻從未改變,當一個人指鹿為馬的時候,剩下的一群人便都認定「鹿」就是「馬」。
在任何一個時代,不管科技怎麼變化,時代怎麼發展,清醒的頭腦依然是一個稀缺品,獨立的思考和高於眾人的覺醒者,一樣都不被認可,但是一樣需要存在。
如果一個群體之中,個別覺醒者都沒有勇氣站出來指出「皇帝的新裝」,那麼這個群體永遠談不上發展和改變。
覺醒者不僅需要頭腦,更需要勇氣,他需要勇氣蔑視權威和群體。
當一群人都在往一個方向奔走的時候,逆行者未必是錯的,所以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瘋子」存在,而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瘋子」存在。
因為能「救救孩子」的人,正是這些「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