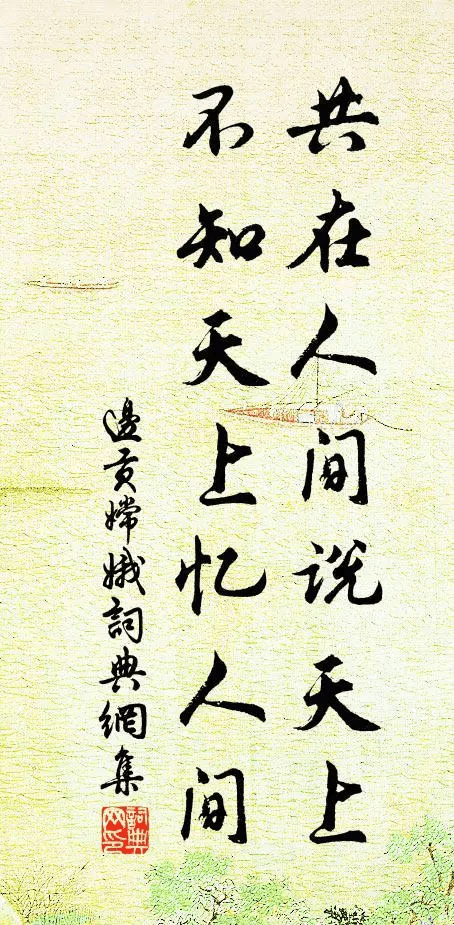秋天終於來臨,幾乎是在一個夜晚裡形成的。人們開始往自己的身體裡尋找溫暖,不僅僅因為它多了幾層衣服的保護,你還可以在那裡找到自己的回憶。
我想起我住在北卡羅來納的日子,那是我生活在國外的第一年,那裡還有好些個像我一樣來自台灣的學生。那時人們流行去國外讀書。不管你怎麼對別人解釋,真正的原因也許只是想出外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秋季很快來臨。我們住在城市裡,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原先前來異國的想像卻偷偷地從身體裡鑽了出來,而我們可能把變得涼颼颼的空氣解釋為新鮮空氣。於是大夥兒決定在一個週末驅車出城,那可是我第一次去遠地遊玩。
我們在上午出發,目的地是位於西邊州界的國家公園,名字是藍嶺山脈(Blue Ridge Mountains)。你不需要收集任何資訊,就可以在自己的心裡為它建構一幅美麗的圖像。我們會先到附近的一個小城Ashville過夜,這是另一個可以帶給你美麗想像的名字。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到達那個小城的黃昏。我們的車子在一路順暢的高速公路行駛了整個白天,卻在將要離開它的坡道上停止前進。我們坐在車子裡,儘可能透過車窗看著外頭的景象。這是一個顯然供觀光客下榻的城市,此時被掩蓋在陰暗的天空下。不知從什麼時候升起的霧靄,打濕了四周的樹木與草地。有一條本地使用的馬路從我們坡道的下方穿過,上面也塞滿了停頓不前的車子。馬路上的紅綠燈依然變換著顏色,兩旁的加油站和旅店也開敞著進出口的車道,好像都做好迎接客人的準備,唯一滯步不前的卻是客人自己。
等到車子終於可以移動,我們開始往城外的方向駛去。車子下面的柏油路逐漸變得狹窄,我們很快鑽進有林木庇蔭的丘陵。當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並且走出車外,立即感到刺痛了皮膚的冷空氣。主人已經帶著笑容站在停車場旁邊等待我們,說我們到的比他預期的晚。據說他夫婦兩人原來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後來畢了業,留在同一個城市裡工作,卻在這個小城購買了一個度假用的公寓。
我們走進去,看到裡面幾乎是一片空曠,只有靠廚具的地方擺置了一張餐桌和匹配的椅子。主人一再說,他們才剛搬進這房子不久,還沒有添購太多家具。其實這樣更好,正適合我們這些同樣缺乏結構的客人。晚餐只是簡單的食物,加上並不特別卓越的烹飪技術。然而這些都是我們開始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好像我們頭上的髮型,以及從Kmart購置而來的服裝。
飯後很多人跟隨主人一起出外散步,想看看這裡有什麼以前沒見過的景象,這讓我想起自己在阿里山的夜晚也曾經這麼做。然而這裡的空氣比阿里山還冷,路上沒有任何行人。空氣裡聞不到飄散的食物味道,也聽不到人們邊吃飯邊發出的歡笑聲。這讓我感覺,這個國家自由、粗獷、開放,但生活在其中的代價是你必須忍受孤寂。這其實是西部電影常帶給人的感覺。然而在電影裡,你可以聽到好聽的背景音樂,有時還是女主角自己唱出來的。然而這裡似乎什麼都沒有,只有越來越寒冷的空氣。
等我們走回房子裡,看到有些人已經坐在睡袋上聊天。我也把自己帶來的睡袋攤開在地上。我沒有聊天的對象,只好靜靜地躺在那裡。跟這麼多人睡在一塊兒,是我只有在軍事訓練時才有的經驗。那時教育班長站在走道上不停地發出警告,如果他聽到任何人講話,就要罰這人出外跑步。等班長的聲音走遠了,我才小聲地跟旁邊的人交換名字,原來住在哪裡。我聽到旁邊的人又跟他旁邊的人交換同樣的訊息。在這兒,我反而沒有機會這麼做,卻也很快睡著了,即使我以為自己無法馬上入睡。
第二天,我們聽從主人的指示,順利地找到上山的道路。當我們的車子行駛在與四周山巒同一高度的時候,霧氣逐漸消散了,天色變得比先前光亮許多。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覆蓋在每一座山上的樹木,都展現出變了顏色的葉子。然而我們無法隨心所欲停下車來,只能打開車窗,讓景物接近我們。好像你只要聞到沁涼的空氣,就縮短了你跟萬物的距離。
雖然有很多車子在我們的前後馳行,我們卻很少有機會看到人,我說的是那些站立在自己兩腿上的人。而且我們刻意避開供遊客坐下來用餐的客棧,儘管它們總是座落在最好的景點上。最後我們找到一個場地,前面有偌大的停車場,後面有逐漸向上攀升的步道,以及放置在其間的野餐桌椅。
我們走出車子,發現這裡沒有太突兀的景色可看。供野餐的桌椅上都沾滿了水,好在我們並沒有任何食物必須在桌上才能吃。四周的空氣依然十分寒涼,我們不自覺地走向一個規模很大的亭子,中間有一個不小的坑洞,裡面已經點燃著熊熊的烈火。你只要隨意轉一下頭,就可以看到亭子的角落還堆積著一捆一捆已經劈開的木材,似乎是免費提供給過路的遊客使用。我們站在那裡不走,逐漸有更多的人向我們走來。大家都站在那裡沉默不語。如果在台灣,有人會好奇地詢問那些有外國臉孔的人從哪裡來,好像那是長久居住在那兒的人所享有的特權。在這裡,卻沒有任何人詢問我們。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也許這是這個國家的特色。人人都曉得要放別人一馬(leave them alone),這是我很快就學會的一種說法。
我們只打算花費一天的時間在山上,不久就捨棄繼續前行,往山下的方向駛去。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經驗,新奇、緊湊、而且累人。然而回去以後,我們恢復原先煩忙與緊張的生活,這才是我們來這個國家要做的事,也是你寫信給親人時第一個會想到的事。接著我們各奔東西,繼續忙碌著只有自己才曉得如何處理的事情。
當我想起這段往事,中間已經跨越好幾年的時光。那時我早已遷移到北部,拿到了學位,在距離紐約市不遠的地方找到我的第一份工作,並且購置了房子,為它添購一些家具,也增添了一個嬰兒,那是我們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小孩。
那可能是星期四或星期五的晚上,我正等待這一天像大多數的日子一樣靜靜地從記憶裡消褪。不久我接到一個電話,告訴我最近從台灣出來的C君將要來我家造訪。他向我問清楚如何搭乘火車過來,說他們到達以後會打電話給我。
C君與我有不少共同的朋友。然而我們真正有機會見到彼此是在我即將離開台灣的時候。那時我與他恰巧做了角色的互換。他本來就讀數學系,後來想改讀哲學。而我本來在哲學系就學,出國以後將改讀數學。為了這緣故,有一天他在另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來到我家,說他想購買我所擁有的那套哲學百科全書。我打算送給他,但他堅持出錢購買。我就收下他的錢。然後三個人一道出外吃飯,我用他的錢來付帳。我以為他會跟我交換哲學方面的意見,很訝異他並沒有這麼做,也許是因為他也不想跟我談論數學方面的事情。
正當我在美國忙著為自己的生存奮鬥,台灣也發生很多事情。C君參與了高雄美麗島事件,是戒嚴三十年以後才發生的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後來他與很多人被捕,並且被判入獄服刑。突然之間,那些不快樂的過去又回到我的腦子裡。在一個即將入睡的晚上,我發現自己開始向神明祈禱。我以為我不再有這樣的需要,就像我以為自己不再關心台灣的事情。然而當你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這大概是你唯一能做的事。
那一年我們參加了不少座談會。其中有一個是在我自己學校裡舉行的。演講者來自台灣一家報社,是個資深記者。她一開始很冷靜地陳述美麗島事件發生的經過,目的是要補足海外人士資訊的不足,她說。最後,她用稍帶遺憾的口氣總結,面對這樣前所未有的變局,政府有不得不採取法律行動的苦衷。
這其實是我好多年以來第一次聽到的華文演講,不確定自己該做怎樣的反應。演講後,聽眾的發言的多半是,他們支持政府的行動。後來有一位女士站起來,用幾乎哭泣的聲音說,國父和革命先烈用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所換來的中華民國不容許野心份子隨意將它摧毀。我突然按捺不住身體裡沸騰的血液。我站起來說(在得到演講者允許以後),我們的國父發動革命的時候也被清朝政府當作叛亂份子。可是這樣的政府反而被推翻了,這是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後會起來打倒不公不義的政府。我這種另類的八股意外地引來很多掌聲。
演講者似乎理解到情況有異,很快宣告她的演講到此結束。在聽眾擁上前跟她對話的時候,我趕緊走出會場,發現入夜以後的空氣變得十分寒涼。我的身子不禁發起抖來,也許是因為我還沒吃晚飯就趕來參加這個活動,也許是因為我的身體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亢奮的生理反應。
然而,時間不會為了任何事情而停頓下來,大家很快又回復到各忙各的生活。即使你不願意這麼做,每年定期變化的季節會逼使你就範。就這樣,時間快速地向前奔馳,沒想到C君已經服刑期滿,而且有機會到國外來訪問。那時候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會這麼做,說這是讓他們有機會充一下電。
接到C君將來訪的消息,我很快想到我忘了留下對方的聯絡電話。似乎有些人即使住在國外,仍然保留台灣的生活習慣,認為他們想拜訪的人家會像店鋪一樣,不管什麼時候都有人在那裡駐守。因此當他們決定拜訪你,必然有人開門出來迎接他們。這當然不是我們這個簡單的三口之家能夠實現的生活方式。我在心裡這麼嘀咕,卻沒有在星期六接到任何電話,或者在答錄機裡聽到任何留言。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們留在家裡不出門,卻依然沒有接到任何電話。我開始懷疑C君已經將我排除在他忙碌的造訪名單之外,但也覺醒到沒有人打電話給我其實是我生活的常態。我開始埋怨自己從來不主動跟人聯絡,才落得別人也不常聯絡我。
黃昏的時候,我們依然坐在有陽光斜射的飯廳裡吃飯。這其實是一年裡陽光最美好的季節。即將遠離的太陽似乎願意花費更長的時間逗留在這裡。如果不是因為等待C君,我們必然開車出外遨遊,有時會開到靠海的那條公路,即使只為了看一看陽光灑落在仍然保持青綠的草坪,以及那棟站立在海灘旁的大廈,孤獨地面對著大西洋。這些景象會讓我想起小時候聽過的一個廣播劇。
然而就在剛吃完晚飯不久,電話鈴聲響了。前次跟我聯絡的那位朋友出現在話筒裡。他說他們已經到達,問我可不可以去接他們。不等我回答,他繼續說,本來他以為可以自己走到我家。下了火車以後才發現,這裡跟紐約的地鐵站完全不一樣。我說沒問題,我這就馬上過去。
我很快到達火車站。這個站其實並不大,這時正被頗為空曠的停車場所包圍。天色正進入昏暗,我先看到跟我聯絡的朋友獨自站在顯目的地方,接著才看到C君被包圍在一群人當中,他們都是我不認識的人。我和C君握了握手。然而在寒暄以前,我必須解決一個問題。與他同來的人多到一部車子裝不下。我說,這不成問題,我分兩趟往返就好。
我先把C君以及另外幾個人放進車裡。在短暫的旅程中,我聽到他說:「這地方跟紐約完全不一樣,感覺這裡才是美國。」我回答:「紐澤西其實是個很乏味的州。有些電影明星嘲諷自己出身平凡,會說他們是紐澤西長大的。」C君說:「原來這地方跟紐約不是同一個州。」我說:「就像台北縣與台北市不是同一個行政區域。」
等我將第二批人載回家裡,我要他們先走下車,然後把車子駛進車庫裡。我下了車,立即聽到鬧烘烘的聲音透過牆壁傳到耳朵裡,好像我正走向一個宴席,而不是我所習慣的一棟安靜的房子。這讓我想到自己在Ashville的那個夜晚,只是現在我改變了身份,成為一群不速之客的主人。
我從車庫的門走進房子裡,發現客人已經在地毯或地板上找到自己的座位。還有人靠在帶來的睡袋上,這時捲成一個滾筒的形狀。我還看到有人在廚房裡給自己弄東西吃。他們說,大家已經在城裡吃過飯。他們只是嘴饞,想給自己做點宵夜。我問他們,現在是不是在學校讀書。他們馬上說,沒錯。然而每個人都表現得像素有訓練的情報員,沒有人會告訴你,他們在哪個學校註冊。這讓我想起在我小學旁邊有個訓練情報人員的基地。我們常常把鞦韆盪得很高,好透過牆頭偷看那些面上戴了白色布巾的人,那時正靠在廊柱上抽煙。
C君仍然被包圍在一群人的當中。他挺直的背脊以及有點誇張的手勢讓他看起來很像正在授課的老師,而坐在他四周的人也把鬆垮的坐姿與歪斜的上身帶到了這裡來。我蹲在外圍的位置上,想聽聽C君在講什麼。然而他似乎習慣在某個關鍵時刻特地壓低聲音。有興趣聽的人必須將身子向前傾,或者請求他再講一次。我無法這麼做,結果聽了半天,竟然沒有抓住任何要點。
有人走過來問我,是否允許他們到後院去。「今晚是中秋夜,你知道吧?」這對我來說可是驚天霹靂的消息。我感到自己像中了樂透一樣,不但有這麼多來自台灣的人出現在家裡,而且帶來了我久違的中秋節日。
我很快理解到,問話的人想知道他們是否可以把椅子拿到後院去。我們並沒有多餘的椅子,只能請他們從飯廳抓了幾把過去。我的妻子看到有人把泡好的茶端了出去,突然心生一計,將我們女兒的那張四方形小桌子也移到後院,充當茶几使用。
我也好奇地走了出去,看到天空上的月亮確實是圓的。坐在自己家的後院賞月,這可是我從來沒有的想法。我記得最後的一次賞月是在我還沒上小學的時候。那晚我們在沙鹿,我跟隨媽媽去拜訪阿桃家。然而阿桃正好去親戚家幫忙,並不在自己家裡。而我們只是暫時住在沙鹿,等爸爸忙完那裡的事,就要跟隨他一起返回安平的新家。
我走回房子裡,問正在看電視的女兒是否想出去看月亮。「圓圓的月亮,跟妳的名字一樣圓。」我女兒的小名是圓圓,這卻引不起她外出的興趣,即使她的那張四方形桌子已經被移到外面去。
我又走了出去,看到原來坐在外面的人正走回屋子裡,說他們要找藥膏塗抹被蟲子叮咬的地方。「外面的蚊子很凶猛。」他們說。現在剩下我自己一個人坐在外面。這畢竟是中秋的日子了,外面的空氣已經有明顯的涼意,無怪乎古人要把它訂為賞月的節日。然而他們忽視了一件事,正像我自己也忽視了同樣的事:戶外的蚊子很凶猛。不久我也感到自己被牠們攻擊,不得不棄守這麼好的一個位置。
我重新回到屋子裡,發現我認識的一對夫婦也自行開車到達我家。那位先生以前是哲學系的老師,現在在一所出名的大學裡教中文。他一向以教學著稱,現在又讀了不少文學作品。我聽到他正在跟兩位學生模樣的女性談論王文興的《家變》。我聽到其中的一位女性說,她無法理解為什麼離家出走的不是那位叛逆性的兒子,而是他的父親。我沒有讀過這部小說,很好奇這位老師怎麼回答。然而我沒有聽到什麼強而有力的論點。這讓我感到有些失望。他似乎忘掉哲學家無論如何都得提出一些具有思辨價值的論證,而不是以他自己對這部小說的激賞作為答辯。然而,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特色,我在猜,特別是當你身在異國的時候。我記得我自己也曾經慷慨激昂地說:「…可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很快感到疲倦了,發現妻子已經帶女兒上樓睡覺。我不記得Ashville的主人陪我們到幾點,我知道我自己無法繼續陪伴我的客人。明天一早我還要送女兒去幼稚園,然後趕去公司上班。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C君比我更早醒來,正坐在餐桌上吃他們自己帶來的麵包。他告訴我,有人已經從外面散步回來,發現我家距離火車站不遠,他們自己可以走過去,不需要我接送。他們很快離開了我的家。臨走前,還把所有的東西還原,包括我女兒的小桌子。
我與C君離別多年的重逢就這樣結束了。在開車的路上,我想到我已經與他走在完全不同的路徑上。我生活在平靜沒有變化的美國郊區,他則一步步走入政治的激流中,而我們還沒有機會好好與對方聊聊自己,以及對各種事物的看法。
當我寫完這些往事,感覺好像是在描述上個世代的事情。後來台灣發生了很多變化,我也在這當兒回到自己的故居地。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完全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每一個人容易按照自己的想像來期待未來,卻不容易接受別人與自己不同的想像。我跟C君仍然沒有太多來往。出乎意料的是,某些共同的朋友也沒有繼續跟他來往。在這個變化莫測的世界裡,人們似乎都在忙碌著只有自己才曉得如何處理的事情。有時候,我會懷念以前那段平靜的歲月以及我們共同的仇敵。正因為它,我們意外地結合在一起,並且天真地以為,只要推倒這個邪惡勢力,這世界就會變得不一樣,而我們就能快樂地生活在一起。
後記:我本來以為自己只是在寫一篇歌詠秋天的散文,沒想到寫出了一段時間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