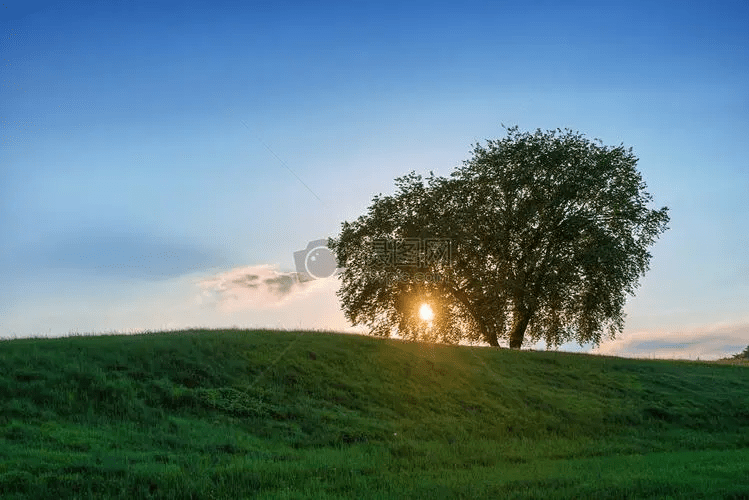我仍然記得我們去台南城裡看爸媽朋友的日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曉得那地方的名字是水交社。從來沒有人向我解釋為什麼它有這麼一個奇怪的名字,包括長久住在那裡的人。然而在那個時代,我聽過不少這類古怪的地名。例如,從我們的村子走出去,如果沿著那條柏油路一直往前走,你會走到一個叫沙灘的地方。然而那裡並不靠海,只是有很多細沙堆積在路的兩邊,幾乎掩埋了整個柏油路。此外,在我們上學的路上,如果你故意走錯路,會走到一個叫酒家還是九家的地方,然而那裡並不賣酒或任何其他東西,看起來也不像只有九戶人家。
水交社位於台南市的一個郊區,在所有房子都快要消失的地方。只有我們要去拜訪的那個眷村,還隱藏在一排鳳凰樹的後面,埋沒在知了鳴叫聲的裡頭。走入村子以前,我們會經過兩家小吃店,都位於村子口的地方。每看到它們,媽媽總會問爸爸,我們要不要先在這兒吃了飯以後再過去。爸爸總會猶豫個好一陣子,這時我們已經走過那兩個店鋪,聽到裡面的收音機正在播報新聞,並且聞到剛從鍋子炒出的菜餚散發出很好聞的味道。
那時我們住在台南另一頭的郊區,需要花費不少時間搭乘公車到市中心,然後換乘另一部公車到水交社。後來我們搬了好幾次家,卻總住在某個城市的郊外,而且總是在爸爸的引領下前往另一頭的郊外看朋友。帶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卻一直是水交社,也許是因為我的心智在那時正開始成長。
我仍然記得,當我們乘坐的公車到達終點站,那已經是太陽高照的中午時分。我隨著爸媽走下車子。我們還沒走出幾步路,那部巴士已經在車掌小姐的哨音裡掉轉了車頭,接著很不情願地撿起一兩個站在路邊等待的乘客,把他們載往市中心,然後在那裡把他們放下來,就像在那兒把我們撿上車一樣。
時代距今久遠,我對於水交社的記憶已經殘破不全。我記得比較清楚的反而是剛下車以後所看到的一條筆直的柏油路。它從我們所在的馬路左邊切出去,在露出了紅土的地面上一路往前延伸,直到快要被水蒸氣模糊了的地方,你才看到一個崗哨模樣的建築。那裡站著一個即使從遠處看都覺得高大的美國人。他的頭上戴著光亮的頭盔,上身穿著筆挺的黃色制服。站在他對面的還有一位個子矮小(但也許只是站著的高度不同)背著步槍的國軍士兵。每一個經過崗哨的車輛都沒有例外地在那裡慢了下來。有的逗留得比較久,有的則很快離去。是否可以離開似乎都由這個高大的美國人用一記漂亮的軍禮來決定。
我不記得這崗哨的後面還有些什麼東西,也許是因為距離太遠,或者那條路從崗哨之後變成了下坡路。似乎沒有任何人知道答案,包括住在水交社的人。我只聽到大人提到那是一個美軍基地。但說話的人講到這裡就不再講下去。不知道是他沒有更多的話可以講,還是意識到我們不該聽那些話,而我爸爸也沒有追究下去。我爸爸從來不會逼問別人到底知不知道答案,不像我們學校的老師那樣。
後來我仍然有機會回去台南,卻從來沒有回到水交社。我重新想到這個地方,是我在美國的第一年。面對一個全新的環境,我其實很少回想過去的事情。我會想到水交社,也許是因為那裡長得比較像美國的模樣。美國的馬路直又長得嚇人,兩邊沒有緊貼著馬路而蓋的房子。有時候,你還會在寬闊的馬路上看到起伏的坡道,好像人們不想花力氣把這樣的馬路剷平。也許是這個原因,水交社那兒的樣貌逐漸浮上我的心頭。現在我還能夠在腦海裡看到,走進那個基地以前也是一條筆直的馬路,隨著地面呈現起伏的形狀,路的兩旁連一棟房子都找不到,完全像我在美國所看到的模樣,而這條路所通往的正是一個美軍基地。
那是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已經在學校上了一整個月的課,並且領到我的第一筆助教薪水。我開著車把那張支票存進學校對面的銀行,順便支領了一些現金出來。想到以後每隔一個月我還能存進一張支票,開始感覺自己已經成為受歡迎的顧客。當我把車子開出那家銀行,覺得應該再做點兒什麼事才好。我對坐在身邊的妻子說,我們去外面吃晚飯吧。妻子並沒有提出反對意見。我猜她跟我一樣覺得這是一個不同於往常的日子。
認真說起來,我們並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事情。事實上,如果加上開學前的日子,我來到這個城市已經有二、三個月之久。我新婚的妻子後來搬過來與我同住。她放棄了自己的學校,因為發現那學校並不提供宿舍,而附近高昂的房租會吃掉她所有的獎學金。離開那個學校就等於放棄她先前累積的學業成果。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的情況。我們就讀同一個大學的哲學系。就在我快畢業的那一年,系裡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很多年輕的教師被除去教職,連研究所也停止招生一年,讓我失去了晉升研究生的機會。我當兵的時候,我的妻子(那時的女友)獲得助教的職位,但很快被新來的系主任解雇。所有的跡象都顯示我們在這個系的前景黯淡。出國是唯一的希望,最好不要奢望再回到這個系裡來。
我很幸運申請到現在這個學校的數學系,並且獲得一份助教獎學金,這是我們兩人此時唯一的收入來源。我不知道我在數學這個行業會有什麼前景。我之所以接受這個機會,除了能夠得到一份薪資,還讓我感覺自己獲得了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機會。然而這是一個甚至很難對人啟齒的說法。人們進入研究所是為了給自己找到一個能夠趕緊加入專業的途徑,我想的卻是我可以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到底哪個世界是我想重新認識的世界?好在我不需要每天為這個理念辯解。數學雖然與哲學迥不相同,它的課業幸好沒有難倒我。我覺得我已經暫且生存了下來,起碼不必在這個月的末尾就要面對人生所有待解的問題。
我已經厭倦在學校旁邊的那家速食店吃晚飯,尤其不想把車子停在那些兄弟會會所的外面。有時候,特別是星期五接近黃昏的時刻,我會看到打著赤膊的男生在草坪上升起了炭火,一旁的地上堆著尚未拆解的啤酒罐,身後的建築還掛著看起來早該更換的布條。這讓我覺得好像闖入別人的隱私空間,而我並沒有興趣這麼做。其實我也度過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只是不覺得我跟這裡的大學生是同一種類的人。
我習慣地把車子駛往家裡所在的方向,卻很快明白我只是遠離可以吃到晚飯的地方。然而我不想回家吃晚飯,起碼今晚不想。我可以想像走進那棟已婚學生宿舍所看到的景象。我尤其不想從自己家的玻璃窗看到還沒有完全暗下來的天色,以及大樓外頭那一片空蕩蕩的草坪,心裡在想這時候的人們都到哪裡去了。我很快想到在我們宿舍的另一頭有個不小的超市商場。或許那裡有提供晚餐的商店。
我不曾開車去那個超市,卻曉得如何從我們所住的地方開過去。我在它的停車場上繞了兩圈,確定那裡並沒有任何食物店鋪。然而從這個停車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馬路對面豎立了不少招攬顧客的招牌,上面已經亮了燈光,寫著看起來應該是餐廳的名字。我不確定那裡面有我想進入的餐廳,然而我們已經沒有太多選擇,我妻子似乎也有同樣的認知。
當我把車子開上那個大道,發現這其實是一個雙向的道路,而且我開進了錯誤的那條線,開始往相反的方向駛去。路兩邊越來越荒涼,建築物很快消失了。我們從40號公路的下面穿過。那是一條可以駛往加州的州際公路。我雖然期待有一天能夠開上去馳遊,卻不想在天色開始昏暗的時候前往冒險。我們又行駛了一段沒有人煙的道路,直到接近一個小鎮才找到調轉車頭的地方。
我開回先前經過的那段渺無人煙的道路,擔心是否能找到原先想去的地方。我們再度從40號公路下面穿過,並且在一個紅綠燈前面停了下來。看到我們已經回到原先應該轉入這條路的交口,我才鬆了一口氣。我在紅燈前面耐心地等待,看到前面是一個下坡道,我們正好停在坡頂上。寬闊的馬路完全展現在我們的眼前,四周點亮了燈光的招牌好像在迎接我們的到來。一種美好熟悉的感覺突然撲向我的心頭。然而我知道我並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方。我才來美國沒有多久,而且剛剛取得駕駛執照。
綠燈亮了,我沒有時間細想。我必須在天色正轉為黯淡的時候找到通往停車場的入口。這不是如想像那麼容易的事,尤其是入口兩邊的灌木叢恰巧遮檔了我可以利用的燈光。我好不容易開進一個停車場,發覺裡面已經沒有任何空位。我開到另一個停車場,立即被那個餐廳漆黑而封閉的外觀給嚇跑了。駛入第三個停車場的時候,我已不抱太多期待。我的妻子卻很快認出那是一個比薩店。比薩是我可以接受的美國食物。我們剛到美國的時候曾經在一個比薩店接受朋友的款待。
進入這家店,我們很快被帶到座位去。坐下來以後,我跟妻子說,很奇怪我們學校旁邊怎麼找不到一家比薩店。然而我很快看出,這不是我想像的那種自助餐廳,而是有侍者服務的正式餐廳。更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看到有一位侍者是我擔任助教班上的學生。即使在這光線不足的室內,我仍然認得出她來。在我的印象裡,她是個好學生,從來不需要我的幫助,卻總能交出無可挑剔的作業。送還學生作業的時候,我留意到她的名字是Rene,就像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名字。於是我認定她是法國人的後裔,這更帶給我一種好感。
好在Rene並不負責照顧我們。即使有一兩次她面向我走來,仍然沒有展露出看到熟人的表情。這讓我覺得,她可能根本沒有注意班上的助教是誰,或者餐廳的侍者不會花時間去尋找自己認識的人。一種更深層的憂傷潛入我的心裡。我想到我在這裡享受晚餐,我班上的學生卻必須在週五晚上打工賺錢。現在我才明白,不是每個大學生都像我在兄弟會那裡所看到的模樣。更令我感到慚愧的是,我在大學裡從來沒有打工賺錢,卻花了不少錢購買洋裝書。四年過去了,我其實一無所成。現在我已經不是哲學系的學生,然而誰能保證我在另一個領域裡就不會繼續蹉跎歲月?
比薩很快被送上了桌。它的味道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好,但足以滿足我已經感到飢餓的肚子。我們開始安靜地吃著。剛才在紅燈前面所看到的景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開始想,為什麼我會覺得以前在哪裡看過這樣的景象?水交社的回憶很快浮現出來。也許是那條通往美軍基地的柏油路帶給我這樣的感覺。然而我從來沒有在黃昏的時候看過它。隔了一陣子,我又想到,我確實在一個將近傍晚的時候坐在雇用的小轎車裡,跟著一群大人前往城中心參加喜宴。也許是在經過那條柏油路的時候,我望了遠方的崗哨一眼。也許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它已經充滿了某種難以抗拒的氣息。我很快放棄這些無益的猜想。事情就是這樣,有時候你就是覺得自己曾經來過一個地方,雖然你明知事實並非如此。
當我們吃完了晚飯並且走出餐廳,我不再感到先前的憂傷。外面的天色已經轉為暗黑,發出各式各樣燈光的物體讓人感覺更加親近。我突然想,我已經不必再去理會那個美軍基地。現在我已經置身美國了,不是嗎?這樣想著,我感覺今晚出外吃飯是全然值得的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至今我仍然記得這個夜晚。也許那是我剛到美國不久的時候,也是我的人生開始做劇烈轉變的時候,雖然在當時我不見得理解這一點。然而仍然有一件事情,我到此時仍然放心不下。那就是,我離開餐廳前,到底有沒有留下些許小費?我真的不記得我是否做了這件事。而且,我當時還不理解美國的習俗,也許沒有想到那些靠打工賺錢的侍者(其中的一位是我擔任助教的學生)必須靠這些酬勞來支付生活的花費。想到這裡,一種憂傷的情緒又回到我的心中,不知道究竟是為了誰而感到的憂傷。